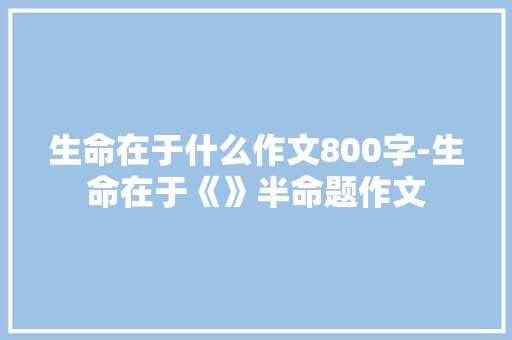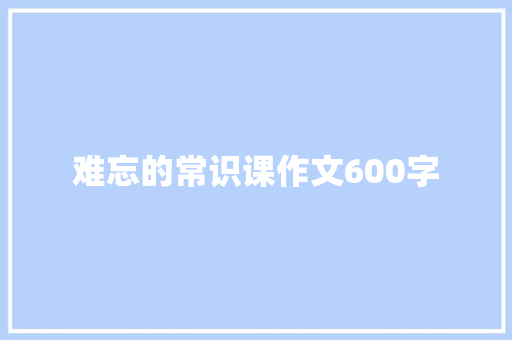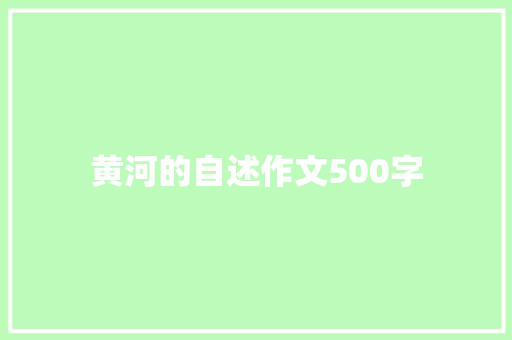这样一条线,在其不断拉长的过程中,抽出了历史,抽出了哲学,乃至艺术,科学,以及文学,我们的荣光,以及我们的勾当。我们反复地讨论着永恒与刹那,但其实我们永远无法获知其中任何一个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是夹缝中的蚂蚁,是半空中的枯叶,我们一直在爬行,但是裂缝像网一样撕开大地,我们一边碎开一边漂浮着,谁也不知道头顶的天穹在哪里固定了边界。
真是荒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讨论存在?我们只是一群不断被风掠走水分的戈壁滩植物,夜幕下,连光线都在我们身上又啃又咬。(投稿 )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还好,我身处黑暗之中。
机舱内,黑暗如同发酵的霉菌一点点扩张了势力,冰冷与清醒从每一个座位的扶手上浅浅划过,从机头到机身,最后流移到机尾,聚在那里,然后不断地发出另一个世界的巨大脉搏。
——扑通!扑通!
“能帮我拿条毯子吗?”我说,我的声带被沁入喉咙的冷气抑制住了。
这里真的是太黑了。只有模糊的线条向我的视网膜反复地表明自己的轮廓,简直如同速写画拉出的直线与弧线,在这忧郁而清醒的机场里上下穿行,相互交错,与黑暗保持最后一点点格格不入。
我抬起一只手,往前伸出。继而听见钢铁质感般冻人的地板上响起了极其有韵律的足音。简直像是鹿。像是冰河边踏碎积冰的花鹿。
我笑了,我在黑暗中听见了一只鹿。那的确是极其美丽的声音,我顺着这足音攀想着它的线条,那些弧度惊人的曲线,细密的黑线,还有更多,还有玫红色的镜框,那片阴影清晰的锁骨,搭在小腹前却绝不与之相贴的手腕,那手腕处突起的骨节。果真是一只鹿。
我的肩膀向前靠了靠,指尖推紧了三四厘米,我准备突破这虚空。
可是我被拉了回去。像是什么柔软得不可抗拒的透明丝线。
——扑通!扑通!
颠簸,颠簸又开始了。我恨它,我记着它。
我看向窗外,窗外雷云游动。
机舱内一片惊呼,就像一座被台风席卷的海岛。
在这去往荷兰的旅途上,我想到了我的朋友,我的高更,我认识的不健全的人们,以及他们如同窗外雷云般闪烁而幻灭的命运——我知道,没有什么线条可以拉住他们,可是他们的每一步都得踩得深陷土地,我不知道为了抬头看天我们竟付出了这样沉重的代价。
我想,如果这真是海岛的话,我或许就是唯一一位海盗,而我的船毁了,它的残骸就在地平线上拉长扩散,最后在日出后被慑人的红光包裹,消化。我失去过一只眼睛,就这样,被消化了。
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偶尔我打着冷战。往事,往事从深色的厚玻璃上渗透出来,然后蜿蜿蜒蜒地流到地板上。我看着它们,感到思绪在沉重的不可思议的时光洪流中穿梭逆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那火光,那道深渊上的火,在一切开始之前就如同点燃卡片一样把我们的人生一一点燃。我望着着自己在窗子上的倒影,那竟也是疯狂燃烧的倒影。
空气中传来嘤嘤嗡嗡的尾音,是机翼快速斩裂夜幕下流窜的气流,我凝视着前面虚空中的一点,想要通过这目光将距离无限拉近——很快,就要到了,我离着荷兰式的阴霾越来越近……
那是2003年的夏天,当一切都还凝固在骚动的炽风中。
我从一所毫无名气的三流大学顺利毕业,荣幸地成为了运往社会的另一枚铁渣。
那时候我是这样与高更说话的。
“如果世界错了,我们就要将它引向另一个山坡!”我在学校社团的活动教室里盘坐在课桌上,双手挥舞,额头突兀,食指笔直。
“那如果是你错了呢?”高更回答我,他的眼斜斜地瞥着我看,就像用一把冰刀阉割我的激情。
但我并没有感到尴尬,高更的话一直让人不愉快,但与他认识的几年里我也慢慢适应了这种像一团扭曲的废铁一般充满了金属棱角感的说话方式。
高更是一个艺术家,当然现在他或许还称不上,甚至他的画作都没有画廊愿意收下,那一张张表现主义的尖牙利齿与红唇绿血毫不调和地互相割裂,一张小小画布上的时空在一道目光中被反反复复地捣碎重组,色调不断地重叠,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无意识中调进了自己疯狂的梦。
我们一如既往开始啜饮啤酒,高更的食指与中指间夹起了细长的劣质烟,那飘起的烟尘中不断浮现着痛苦彷徨的面容,像是一百张面具的破碎,玻璃扎进双眼。
脚下,扭曲的易拉罐被零零散散地丢在散乱的课桌之间,啤酒的味道在大风中挥发。
窗外,积攒的云霾正加速回旋,让人感到天空的巨眼即将裂开。
“我说,天气预报里讲的是今天来台风吧。”我对高更说。
“是的吧,等了好久呢。”
“等?你喜欢台风?”
“喜欢嘛也不能完全这么讲,当然心里是挺期待的,但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的喜爱,毕竟也不是邮票、电影、艺术品什么的。”他说。
“这团稍纵即逝的玩意,既没什么收藏价值,于人于事也毫无益处。”他摩挲着下巴,就像摩挲一颗坚硬光滑的铁球,“怎么说呢,那只是美吧。我就是这样给它冠名,给它定性的。”
高更依靠在桌角,用动物般的眼神看我的瞳孔。
“我也并非什么气象爱好者,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它的美啊暴烈啊自由啊色调啊这样的属性罢了,只是自己心里喜欢罢了。”
这话说得简直像是一句哲学宣言。
美与暴烈,自由与色调。
“是嘛。”我搜罗着合适的词语,并且在脑中竭力构造着一副台风的画面,将其与我记忆中的某些东西对比。
“这么讲起来,我的话,或许也喜欢过跟高更你讲的类似的东西,”我说,“它在感觉上与台风差不多,说是具象吧又找不出具体的形态,但如果称之为抽象,那也不妥,因为毕竟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事物,而非什么观念性的东西。”我拉开了我惨白的画布,用调混得极其斑驳的绿蓝色往上面硬生生的甩。这多像高更讲的那般——美,与暴烈。
“大约还是孩提时代,对,就是那个太阳显得特别大,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总觉得自己异常而奇怪的时代。”我说。
“那时候啊”,我心里想着,“那时候我还没有这样四处漂泊,我还没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不分昼夜地乱窜,不知道是在跟随谁的足印,简直是留着追日夸父的血脉的孩子。”
是的,那时候还没有呢,那时候我还奔跑在出生的土地上,我还不知道,原来这荒黄的泥沙竟通向了作呕的沥青。
“那时候,我也还不是我,我还很单纯,我也没那么自我,我只是个畏惧阴影黑暗,畏惧夜晚与长辈的鱼。我在这小小的清池里打转,我的梦如同水上的桃花,我只是鱼,我不必游向远方。”我这样想着,我想我那时候只是条鱼。
我至今对那条路念念不忘,那条路是我人生中未再有过的奇异景象。不像现在,现在你走在街上,每一处都罩满了一种现实的灰冷,每一处都是现代的灰冷,那些漂浮的尘埃不断积聚,空中落下成千上万个表示服从的符号,天空就像死了一样。
那条路上地面从未出现过任何温顺的色彩,那些坑坑洼洼的反射全面缀满了深色的光彩,简直如同某个苍老男人浑浊的眼珠一般。
那天我的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路上,头顶的天空被蓝色与白色的断片不断重组着,色彩之间的交界线被什么泛着空虚的雾气给交融了一样。我左右顾盼,路的两旁长满了不知名的矮树,躯干与叶片被深绿浅绿包裹着,里里外外地向上扭曲爬升。
我低头蹲下,不知从哪个地方射来的阳光搓揉着我的眼角,使我周围的事物立刻变形,渐渐虚无淡化,乃至被一片金白取代。我向视野的中心聚拢注意,只看见一湾水涡在急剧放大,回旋打转直到令我生出海的错觉。
这时我的父亲叫了我一声,那声响如同一道飞矢从什么遥远未知的地方跨过千山万水直至我的耳蜗,像开阔荒野平地上骤然劈开空气发出焦味的一道闪电。
我抬起头向父亲望过去,看见他向我伸过来的手掌滚动着阳光轰炸下的阴影,像一只扑食的飞鹰盖住了我的头。
“走吧,我们还要去找它呢,”他不紧不慢地说着,好像在与言语的韵律调情。
我嗯了一声,然后跨过那水涡,向已经迈出两步的父亲追去。
我与父亲都向着阳光行走,那时候,光线的密集程度令我不断联想起宇宙中被粒子流轰中的宇航员,我与父亲就是那追逐星球的漂流者。
我抬起手看腕表上的时间,指针指向十二点,我想这时候城里的行客应该正在半梦半醒之间接受的沉睡的召唤,那是下午前溽热的昏睡时刻。
父亲回头看着我,表情模糊不清,当他背着阳光时脸的轮廓被波动的光圈匀过,那张脸充满了奇异的疏离感。
“你看。”父亲指向远方的平原。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起伏的原野上花朵被不断地撕开,在原野的上空正流驶着紊乱的气流。在离地十多米高的地方,轻浮的枯枝与被折断的花叶顺着气流往上盘旋,简直像从大地的眼睑里向上抛洒的泪滴。那随着呼啸的风声逐渐团聚起来的气旋令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即形成。我感到它的勃动。
“那是一场风暴正在形成。”父亲说。
这时候我看见父亲举起了他一直贴着身体的右手,他拿起了他的照相机。
“我们走吧,”他说,“去看看。”
然后我们跑了起来。
父亲生于荒唐而动荡的年代,他的前半生始终与荒谬脱不开关系。
他不修边幅,头发总是很脏,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老是在一刻不停地挠头。
“你什么时候回来?”
在我不多的记忆里,我总是这样问他,而他总是以笑作答。
他是一个摄影师,在八十年代的浪潮中也曾迷恋于诗歌,但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对此却不再
提起。
有时候我会故意扯到这个话题,向他问起。他就这样回答我:我感到自己已经经过了一个阶段,不再有那种冲动了。
当然,他依然写诗,只是已经不再如同年轻时一样充满激情。
他喝酒,但是没有瘾,不吸烟,因为害怕。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怕死的人,他极其爱惜自己的身体,为此自私一点也无所谓,但令我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会不要命地乱跑,拍照。
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他的疯狂的,有人说他是疯子,但他却悲哀地说他早就疯不起来了,他说自己的倦鸟,总是在追逐橄榄树林里的一阵悲风。
他结婚的很早,只是不知道生我的女人究竟是谁,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这种谜团式的宿命早早就在我降生的床边等待着我了,我知道,接下来就是一场漫长到我无法呼吸的拷问,而我也宿命般地继承着父亲的自由与梦。
我知道,他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人,在他的身边他的父母他的女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长期生活,因为他无法属于哪个人,他不是社会可以限定的,也无法被人束缚,仅凭爱是无法捆绑他的。
这样一个人,我早该预料到他的结局。早就有人说过,林先生是不会长寿的,就像革命者都是自己先被革了命。
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以片段的形式插入我的生活的。他不常回家,一般一个月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家里,这样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一开始一个月回来十天,然后就只有一个礼拜,接着是只有三四天,到最后他一年也就极其隐秘地出现几次,像不定期飘回坟墓的鬼魂。
到了最后,他就像一只养在乡下的猫一样,越来越少回家吃饭,最后终于消失在莽莽山林间,像某个不曾出现过的幻影。他失踪了,在一场风暴里,他在追逐他归宿的路上像一行风沙里的诗句一样被抹杀在时间深处。
“那是什么?风暴?”高更继续小口地啜着啤酒,但他的脸已经红了起来,我有种感觉,在他喉结上下鼓动酒液冲进胃袋时,他的软发似乎正在一点点舒展开来,像特定时刻里他的灵魂的外在显像。
“对,就是一场风暴。他就是在一场风暴中消失的。倏地一下,发灰的白色遮住了他的身影,就这样,他消失了,没留下一点声音,甚至连图像都没有。他带着他的相机一起消失。”
“嗳,那风暴究竟是怎么回事?”
“风暴啊……”我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坐回椅子,随着这“啊”这音节的不断拖长,我倚靠在椅子上的身体也逐渐松软下来。
“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说。
我想起很多东西,有些画面——那个场景的颜色,那个人说话时口型的浮动——难以想象,我竟然依旧感到如此的新鲜。
“那是冬天的街头,那天距离他上一次回家依旧有十七八天了。我手上握着零钱,身上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口中吐出的白气像烟一样将我的面容模糊得极其苍白。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形象,我握着钱,去买书。
冬天的下午,在雪停了以后,人会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干燥,其实我现在也弄不明白那究竟是真实的干燥,还是心的干燥。
我一边舔着嘴角,一边拐入西街。
我低着头,以极快的速度向前走着,眼角紧皱,目光在脏雪上游移,我正数着地上的脚印。
在越过第六个电线杆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鞋。
我怎么能忘记他的鞋呢?那双磨损得那么厉害的鞋,穿在他的脚上踩下去时会啧啧地响的鞋。
但我还是楞了一秒,或者是两秒,我不知道,那个瞬间我似乎失去一种对时间流逝速度的判断。我感觉到屈辱与悲伤正鬼叫着往我身上爬,它们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爪印。
我想可能是我打破了一种惯性。我因为习惯了与他长期的疏离,所以不会感到任何难受,可这时候,那种在大街上冷不丁碰见久而未见的父亲的悲哀在我的眼底突然就烧了起来。
有时候我会想,每个冬天都要烧这么一把火,而燃料总是我们不愿面对的东西。”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你哭了吗?还是跑走?”高更摆着手问我,啤酒在易拉罐里来回滚动。
“不不,没有那样的事情。他把我带进了咖啡馆,我脱下衣服挂在磨得发亮的衣架上。然后我们对坐着交谈。”
我大概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想着什么,但我还记得自己内心翻涌的情绪。我们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风从上面的窗子里灌进来,但仅仅吹进来半米就散开了。
那时候的咖啡馆并不现在这样的,那只是一家很小很破旧的店,墙纸有一小半都是脱落的。
父亲穿着蓝色条纹的风衣,眼镜上面有十几道细小的霜花在交错纵横。我始终看不清那双眼睛。
男侍者端上咖啡,将杯子摆在我与父亲之间。两道热气就这样一直一直往上翻滚。我看着它们就像看着透明的墙。
“知道风暴?”父亲突然这样问我,毫无征兆。
“风暴?”我当时就像高更第一次听说风暴一样感到奇怪。
“风暴,那是我追求的极致的美之一,是自然最强大的风。”父亲说,“有的人常常能遇见它们,但有的人一辈子都看不到。”
“你见到过?”
“对,我见到过。在很小的时候,很小很小,我大概都忘了自己几岁了,那应该我记事前的事情,我每每回忆起来只能看见一闪而过的画面,只有一点模糊的残像。但即使是那残像也足够我震撼的了,我看着那团呼啸盘卷的气流,目瞪口呆。”
“你是怎么见到它的?”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但我还是打算问下去。
“是我的父亲带我去看的。”
“爷爷?”
“对,是他。我们当时走在一条奇妙的路上,你爷爷走了过来,在阳光过分强烈的中午拍了拍我的头,然后把风暴指给我看。”
我听到这段话,顿时感觉脑中有一道电流划过,头颅里酥酥麻麻的,像有什么长眠未醒的东西要睁开眼睛了。
“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我走在奇妙的路上,看见了风暴的诞生,简直是从美通向美!”
父亲说着摆起了双手,像在抓着什么一样,指尖来回移动。
“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生命一定是奉献给这个东西的,我要抓住它,我要把它拍下来,你知道吗?”
“不过有一点,”他说,“有一点你要记着:世界上有两种风暴,一种是黑风暴,一种是白风暴。”
“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命运:白风暴带走你,黑风暴送回你。”父亲说,他说话的样子如同一个法官。
我在那个冬天的下午听见了这句话,这句如同谜语的话。我还听见它随着冷暖变化的气流飘出窗口,在那个白光迷蒙的下午一直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白风暴?黑风暴?
是白风暴带走了父亲?
黑风暴又能还给我什么?
下午光线昏暗,教室里课桌凌乱。
窗外的榉树叶片被风频频带起,打着小旋散开。天空中浓重的乌云正在聚拢。
“然后呢?”高更问我,“跑起来之后呢?你去了哪里?”
“我们追了过去。父亲嫌我跑得慢就把我抱了起来,托在怀里并继续追向那风暴。
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件事发生在几岁了,但我知道我当时很小,非常小。
那时候周围的叶子都停止了摆动,我听见呼呼的风声一刻不停地刮过头顶,但可怕的是我就是见不到那些该有的摆动。
父亲一边抱着我跑,一边告诉我,那是风暴来临前应该有的状态,小风都消失了,大风在我们头上的高空滑动,更强烈的气流都被风暴掠夺了。
我看地上的水洼陷了下去,积水正在有规律的震颤,最后一点点阳光映照在上面,我恰好看见了我自己扭曲的脸,也不知道是因为惊恐还是因为水面的波动。
父亲继续跑着,而我则感到呼吸的窘迫,我努力向外呼气,又努力把不再温顺的空气吸入胸腔,但我的肺里似乎产生了一股排斥力,竭力拒绝了这躁动的空气。
我闻了几百米外的某种腥气,它的源头大概已经被风暴的余波绞碎,而逃逸的气味正顺着温和无风的地面爬行。
“爸爸!”我感到异样的惊恐,被腥气塞满的肺剧烈的抖动着。
父亲没有理我,他只是继续跑着,只是跑得越来越慢,身体压得越来越低。
我目测了一下,我们距离风暴大概还剩三百米,而那团可怕的气旋已经呈漏斗状不断将触须般的旋转气流伸向地面。
大地上又起了一阵大风。树叶重新开始哗响。
“爸爸!”我又叫了一声。
我看见了前面的水坑里的水平面已经被吹得向我歪斜,剧烈撞击我的大风将我身体里不多的热量一点点掠走。
我定定地注视着漏斗状的风暴,天空中几只迷途的雨燕正被它无情的吞噬,凡是被它的尾巴击打到的鸟类都将在瞬间昏迷过去,无论是一只燕还是一只鹰。
父亲的步伐此时开始出现了紊乱,我从身体的颠簸程度感觉到他的脚步正在变得一深一浅。
我用手搂住父亲的脖子,连手指都紧紧扣着他的肩膀的肉。
我的声带开始发抖,我感觉到寒冷也在此刻侵蚀着我。
“爸爸——!”我绝望地喊着,声音飘出几米就消散在虚空中,被冷气竞相分食。这一声我已经带上了哭腔。
眼泪已经不再受我控制,那冷风一激就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
我开始对父亲产生轻微的怨恨,但很快着一丝薄如细烟的怨恨就随着一种死亡的觉悟而泯灭了。
我开始想到了死,但我那时极其幼稚的心智还不足以思考这样的事情。
于是那恐惧与觉悟又转化成了对风暴的庞大的怨恨,它驱使着我与风暴四目相对!
“风暴——!!”
我咬牙切齿地喊它的名字,我他妈只喊了一句,那白色的手掌就将我与父亲镇压。
——风暴!!
我昏了过去。”
随着我吐完最后一颗字,高更的易拉罐也停止了摇晃。
风从外面吹来,路过易拉罐的开口时发出呜呜的声响。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都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与令人压抑的黑云,一言不发。
是高更先打破了这安静。
“然后发生了什么?”高更握紧了易拉罐。
“然后我醒在温暖的床上,像回忆梦境一样回忆着一切。此后这段记忆仿佛被镇压了一样,不知到那天才苏醒过来。”我一边说一边凝视着眼前的画布,从聊天开始现在我只画了一笔。
“而我,”我说,“我也在短暂的清明后恢复到那个年纪的小孩应有的混沌状态,直到我开始记事,人正常地开始思考。我想距离我第二次思考死应该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了。”
“那你父亲呢?”
我想了一会,然后手以一种不确定的颤抖伸向了黑色颜料。
“失踪了呀。”我说,“从那以后就失踪了,像乡下的猫一样,失踪了。”
“一直到今天?”高更那双深色的眼眸望着我问道,但他又时而看向我身后的云层。
“嗳,你说,那像不像黑风暴?”高更突然指向窗外,那手指的样子简直与父亲当年指给我看风暴的样子如出一辙!
口鼻间忽然传来了遮盖了酒味的腥气,我望向窗外,发现那里一团漏斗状的黑云正在越集越密。
“啪!”
我的笔摔在画布上,上面一片漆黑。
我的父亲没有死。
现在,他回来了。
杭二东河高二(11)班梁靖吕
感谢阅读《风暴》小说,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美德网的支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熊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