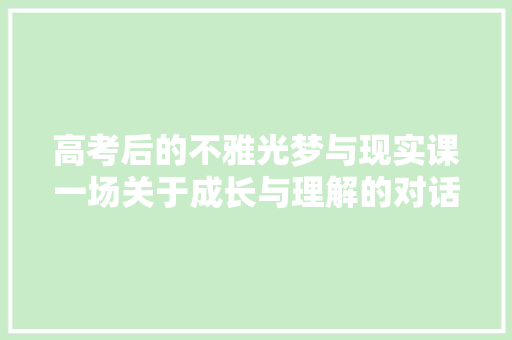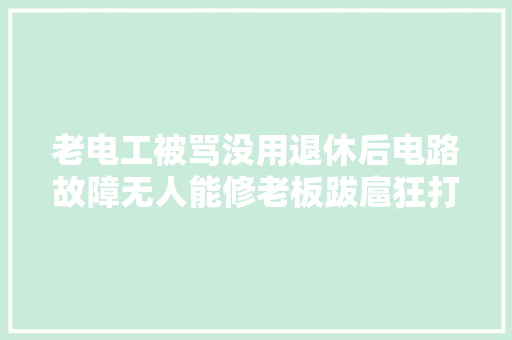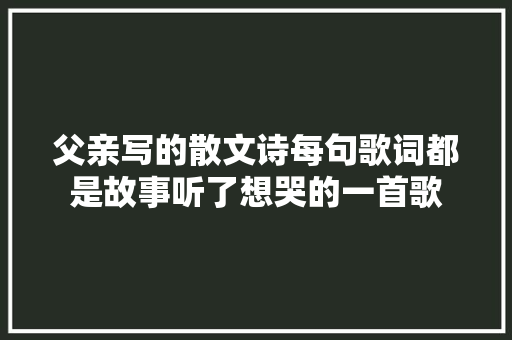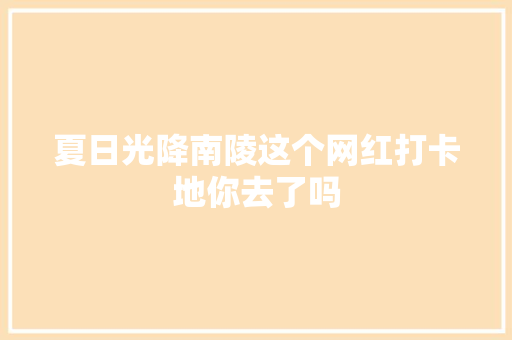◎张四清
记得父亲拜别的那天清晨,天空阴沉,景象郁结。我及早去医院听医嘱、具名。他下午有个脉管炎的小手术。家里离医院并不远,路上人流车流也少,但是车行在路上,我内心竟有些莫名的心慌,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我的车无端的撞到了路边的防撞杆上,这对付有廿多年驾龄的我来说,却是十分意外的。事后想起,这彷佛该当是父亲要拜别的不好征兆,只是当时我完备没故意识到,不然我当时会多陪陪他,不至于事后留下终生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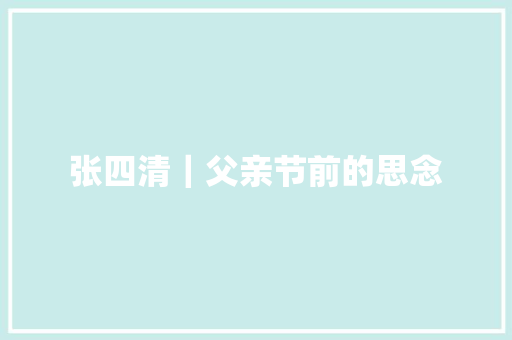
弃车直接到了医院,大姐正陪着父亲吃早餐。我匆匆赶到年夜夫办公室办理了术前具名等手续,急忙就要出去牵车到修理厂,途经父亲的病床时,只大略跟他打了声呼唤就准备走了。这时,我忽然创造父亲神色凄婉,他对我欲言又止,眼中满是不舍、留恋乃至还有哀伤。我内心一凛:这是怎么了?父亲动手术也不是一回二回了,而且哪一次的手术规模也比这次大,我还从没有见他用这样的目光看我,我当时担心车停太久,造成道路堵塞,也未及细想,就对他说:我把车牵到修理厂就回,你这是小手术,没事的,放心。
我匆忙焦急地赶到修理厂,刚停车不久,大姐的电话来了:父亲弗成了。我大吃一惊,火速赶往医院,等我来到他的床前,父亲的身体已经冷凉了,这时,离我跟他分离不敷三个小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三小时,仅仅只是三个小时,竟然造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生与去世之间遥不可及的间隔。真是造化弄人!
我呆立于他的床前,看到他苍老安详的脸庞,看到他再也无法睁开的双眼,我肝肠寸断,无语饮泣。他生前曾说:我就算去世,再也不想开刀了。他生平刚烈取信,至去世,他也没有让动那一刀。他享年89岁。后来,每当我想起他离世前的情景,他离世前看我的目光,就象锥子一样,一贯刺痛着我的内心。
我是父亲的幼子,独子。他40多岁才有我。据他生前常常讲,我出生时,只管那个时期物质极其匮乏,家里也不富余,但他还是满请了乡亲众邻到家喝喜酒,为我做满月。我的出生,给他这个穷苦的、毫无生气的田舍带来了欢快,给他这个屯子的中年男人带来了无限希望。
他是个粗粝的村落汉,可是对付他的幼子,他无时无刻无处不流露出他的优柔和爱意。
春天,他可以放下手中急迫的农活,在田畈里追逐几里地,只为了抓到一只野兔,而后耐心地在自家后院为兔子垒窝,让自己的爱子和野兔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而他,则蹲在一旁,笑眯眯的甚是知足。炊烟恰好在此刻漫过后院,母亲已经在院子里摆下了桌子碗筷。
夏天,他在自家后院挖出一方小小的池塘,池塘里种上荷花。塘里有清蛙,小鱼游耍,荷花周边有蜻蜓和蝴蝶飘飞,荷喷鼻香溢满了全体院子,我时常在院里扑蜻蜓,采荷花,小人儿的心里充满了愉快和快乐。我常想:我至今不改的田园情结,是不是他那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秋日的夜晚,他牵着我的手,去村落头看望爷爷奶奶,在回家的路上,由于我得到了爷爷奶奶的许多褒奖,他的心情格外爽快,脚步也轻盈,嘴里还时时哼着小曲。此时,月在中天,月光溶溶,秋虫唧唧,夜色如水,空气中飘散着丹桂的喷鼻香味,还和着泥土的芬芳,我们父子俩牵手走在乡间小路上,其乐融融。那个梦幻般的景致,已经深深地映在我脑海里,诗意了我许多年,一贯至今。
冬天,窗外白雪皑皑,朔风呼号。室内热气腾腾,喷鼻香味弥漫。他和他的弟兄们在室内打糍粑,准备过年的年货。只管他单衣薄衫,挥汗如雨,他总也忘不了把打好的糍粑,时时时揪一块,送入我的小嘴,满是期盼地问我:喷鼻香吧?那种带着他汗水的喷鼻香味,那个热气腾腾的场景,成了我此生挥之不去的甜蜜影象。
我的童年,就这样一贯是在他的宠溺中发展的。只可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与他逐渐有些疏离,我们没有能够成为传说中的父子心腹。这是我的遗憾,也是他的无奈。
昨夜,我又梦到他了。他还是那样精壮、干炼。他带着我和母亲到一处建屋子。那里那边所草木葳蕤,流水淙淙,蓝天白云,空气新鲜。确实是一神仙寓所。在梦里,一家人都不言不语,但都面色喜好,神色轻松。我醒来时茫然四顾,心内痛惜。心想:我是惦记父亲了,还有可能是父亲也在惦记他的幼子,他只能把他的思念幻化成梦境通报给我?而梦毕竟只是梦啊,可怜天人永隔,今生,我们父子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欲翠青山起父茔,
难别盛世舍亲情。
从此慢步重宵九,
再见音容梦几更。
父亲节就要到了,这是我迄今为止说给父亲最多的一次话了,是为祭。愿天国里的父亲能够收到。
(编辑:高一平)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张四清,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生于1966年。烟台散文学会会员。现从事市政工程,私业务主。爱好文学,业余从事诗词散文创作,曾在"大众号及文学刋物上揭橥诗词散文多少。
壹点号烟台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