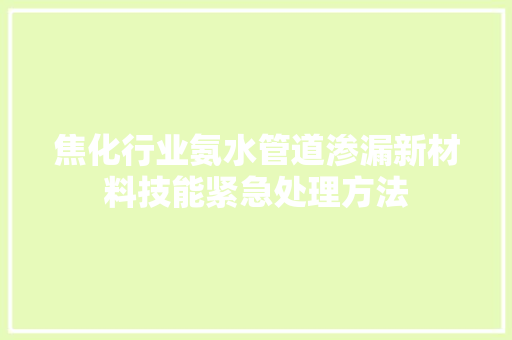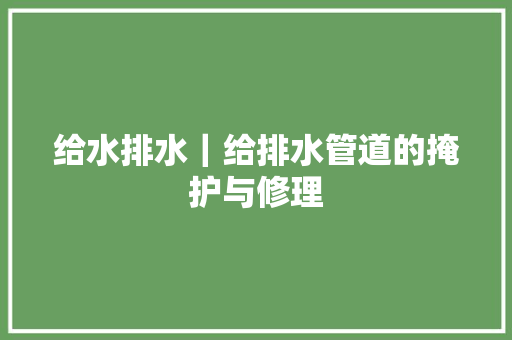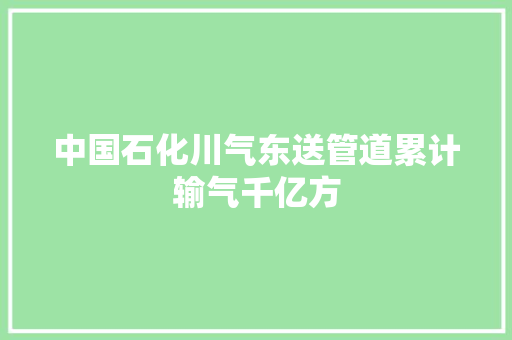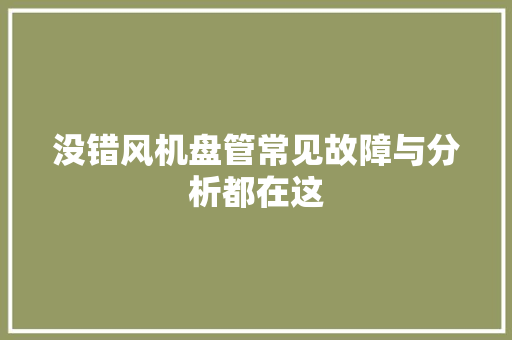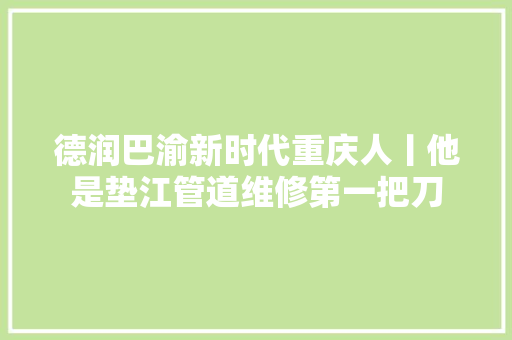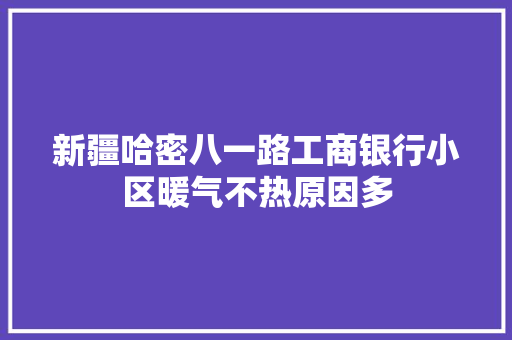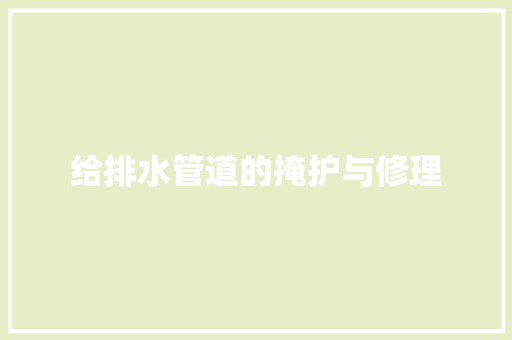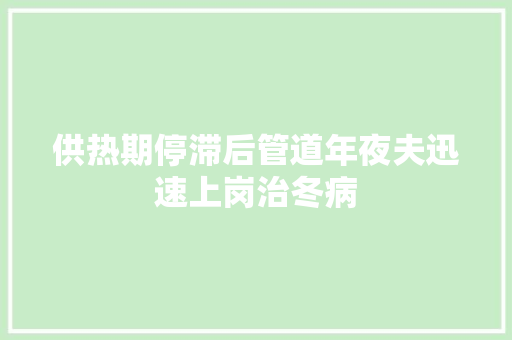越往前走,你不一定是走进繁华,而是走向荒漠。
正如网剧狂轰滥炸、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年代,

我却执着地抱着琼瑶姨妈的《情深深雨濛濛》哭得稀里哗啦,
一边回味着一场场惊世骇俗的你侬我侬,一边骂着:书桓,你真渣!
本日的故事也要从江南的一场雨提及。
此刻,男主正咬着笔杆,看着窗外阴霾渐起,淅淅沥沥,
心里是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老丈人的影子无情在心里徘徊。
他不知道拿什么去见最爱的女孩。
江南的小雨,总是有这样的魔力。
一场雨染得梨花白、杏花红,
僧庐下、客舟中,
不知缭乱了多少人的思绪,打湿了多少暗黄的纸笺,
只要你乐意听,油纸伞下总是有故事的。
他暗恋的女主,姓管,家道殷实,家学渊源颇深。
听说祖上便是辅佐齐桓公成其霸业的管夷吾。
功成身退,为避战乱,才从山东移居到浙江湖州,祖祖辈辈定居于此。
管家人品极好,大方仗义、年夜方乐施,
风调雨顺的时节,开馆授徒;
荒年饥岁卖画换钱、赊粥捐粮,倒骑着驴子,看看山茶花。
乡间邻里都说其慕古贤之风,便将此山称作“栖贤山”。
吴兴山麓栖古贤,山茶花间住神仙。
和煦的山风,就这样伴着花喷鼻香,撒下繁衍生息的种子。
在这样家庭中发展起来的女子,自然是超尘脱俗、地灵人杰的。
幼年时的女主总是眨着大眼睛,细细地听着父亲的教诲,一字一句,一笔一画
倚窗诵经,不雅观花弹琴,静似红蕖照水,动若细柳扶风,
书得行草真隶、画得梅兰菊竹,
佛心一点,仪态万端,
犹如瑶池仙子宴流霞,醉里遗簪幻作花。
管公唤她作“瑶姬”,并暗暗起誓,不能让凡夫俗子作自己的女婿快婿。
先生长西席无边丝雨细如愁,没想到千里姻缘一线牵。
可堪那好雨知时节,
润物,也当红线。
【画】
1290年,他出山寻友扑了个空,忘却今日竟是惊蛰,没带着伞。
原来是群山叠翠、绿蟒翻滚,天却顷刻间变了脸。
春雷乍动,只得在城郊的瞻佛寺暂避存身。
好在寺院方丈也是他的故交好友,可借得蓑衣笠帽,免了这一身狼狈。
不久,雨停风息,他刚要走,却不由得停下脚步,望着寺院的墙壁入迷。
钉住他的,是墙壁上的一幅《修竹图》。
但见图中,墨竹一竿,从左下斜刺至右上,苍劲挺立。
竹叶用墨以浓为主,却也讲求,虽本体较少变革,也恰好和竹竿对照生姿,
造型上,肥不似桃、瘦不似柳,下笔爽利娟秀,枝叶纷披,错落有致,匠心独运,已臻妙境。
“好气概,妙手笔,非功力深厚而独到之男子所不能为!
”
看着看着,他不由得叹出声来。
“雷动惊蛰始,雨催龙鳞升,没想到敝寺今日,竟迎来真龙。
能得‘吴中八俊’一语,可见此物当真不俗。”
枯荣方丈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不敢不敢,晚生敢问这画出自何人手笔?这山村落野店之间竟还有这般人物?”
“哈哈”枯荣大师朗声大笑,“时听子昂所言,说此画是男子所为?”
他瞪大了眼睛,诧异:“难道是女子?何人啊?”
“子昂可听过,栖贤山管伸,管太公?”
“管太公之女?”长老点点头。
管伸的大名在他,早已是如雷贯耳。
此公吴兴一带名望甚著,当地贤达也多有交游。
他曾经在酒席宴间,也与管公有过一壁之缘,
可管公有个如此才华出众的女儿,却实未知,这不禁激起他的好奇心。
“如此才学,待字闺中?”,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点酡颜。
长老听完,眼望着面前这个器宇轩昂,眉宇间还透着半分帝王气的年轻人,
卖了个关子,笑道:“神女生涯原是梦啊。”
梵音阵阵,木鱼声声,众生万物却究竟参不透一个“情”字。
回到自家府邸,男主平生第一次以为,
廊下的阳光如此灼目、书房的地面犹如火烧、手里的羊毫非常的沉重。
他一次次挥毫着墨、刷刷点点,意图再现寺中《修竹图》的风采,却终未成其事。
要知道这在平时,是他不屑为之的事。
让他牵肠挂肚的除了维妙维肖的图画妙笔,还有老僧口中的那位管家小姐。
“我究竟该若何才能见上小姐一壁呢……”
想着想着,他便在梦里巫山神女相会了。
院中的雾霭散了,雨滴从叶脉上滚落,拨动着大地的琴弦,有什么东西在悄然萌动着。
【书】
卷轴用一只精美的锦匣盛着,送来锦匣的是管太公的朋友。
朋友解释来意:赠书人想让管公指示一二,
并想用锦匣中的这幅字,换二小姐的一幅墨竹。
管公好奇,打开卷轴的第一眼便落在了题名上。
三个遒媚秀逸的楷书赫然在目:“子昂書”。
宋末元初的江浙一带,
作为末世皇族、秦王赵德芳的嫡传子孙,赵孟頫(字子昂)自然是名满天下,
这不仅源于先人的荫蔽,还源于其足以睥睨天下的才华。
他年少成名,14岁便经由吏部选拔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
1276年,蒙古铁蹄攻陷临安,国破家亡,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弃职闲居,
元廷几次征召,盖不履新,甘心含恨林中。
其人生的剑眉星目,风骚洒脱,
其诗文文词高古、字画得钱选真传,交融诸家之妙,精工绝伦。
史官杨载称:
孟頫之才颇为字画所掩,知其字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
当然,这是后话。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看到如此崇高而遒劲的书法,管公对其为人已是懂得半分。
此书筋骨内含,笔笔精到,他自然也是爱不释手,
毕竟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千金难求。
管公对赵子昂的要求欣然应允,心中暗道这年轻人的聪慧:
其一以书换画,抬高了双方的身价;
其二,以书易画,凤子龙孙亦不显冒昧,可避男女之嫌,可全斯文之礼;
其三管公早听闻这赵官家出身帝胄、温文尔雅、一表人才,
常怀经纶之志,素有八斗之才,岂不借此良机,撮合这一段金玉良缘?
谢过朋友,管公便将书法第一韶光拿给女儿,解释意图。
年轻的管二小姐,看看精心装裱的书法作品,又听父亲诉说赵子昂的平生为人,
常以李清照自诩的他自然甚是钦佩,只恐这位赵官家不似当年的“赵明诚”。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她便立时提笔,将心中的“竹”描摹得维妙维肖,
每一片竹叶都像是一片未启的唇。
在心里红得如火,在纸上黑得如漆,
如胶似漆。
鸿雁传书,见字如晤。统统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随着墨竹图一起来的,是管公的一封报答宴的请柬。
看着几案上的两样东西,那赵官家若说是坐立难安,不如说是欣喜若狂。
惊鸿一瞥,抵得过似水流年啊。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且奉上一篇《修竹赋》
猗猗修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
操挺特以高世,姿洒脱以拔俗。
叶深翠羽,干森碧玉。
孤生太山之阿,千亩渭川之曲。
来清飙于远岑,娱佳人于空谷……
【诗】
一见美人兮,思之如狂;
人间无正色,悦目为姝。
红笺小字,和人间情爱比较,自然是诉不尽平生意的,
但有了绵长的文化和高雅情致的浸润,
婚姻便不再是罗网,而将两人的心扎得更紧了。
1262年,管道升终于得偿所愿和赵孟頫喜结连理,
彼此过上了赌书泼茶、诗书唱和的日子。
这一年,管道升28岁,赵孟頫36岁。
大概是前缘注定,“管瑶姬”变作“管道升”的那一刻,
她也继续了先人优秀的基因,
前世为贤相,今生作贤妻。
赵孟頫出于母命,不得不与元臣程钜夫,北上大都,做起了南宋的“叛臣”。
(程钜夫曾向忽必烈透露,如三次征召赵依旧抗命,便会将其百口处以极刑)
声名显赫、官运亨通,从兵部侍郎到翰林院承旨、荣禄大夫,
赵孟頫历仕五朝,官拜从一品。
延祐四年,连管道升也变成了“魏国夫人”,世称“管夫人”。
官帽越戴越高,人却也越来越孤独。
刺目耀眼的富贵荣华背后,是背国忘家、数典忘祖的诋毁。
他读的儒家经典越多,心里的负罪感就越沉重。
意思有点像《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公子。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以是,他屡屡辞官,或者调请外任,
做做教诲、管管民生、和四方学子谈经论道,
连衙署都设在了山净水秀的杭州。
让历史的困惑和压抑回到书卷和山水间荡涤和纾解。
名利耗着人,文化养着人。
他比谁都明白,
自己是南人的魁首,也是傀儡,是昭显礼贤下士的旗帜。
自己不真是元世祖嘴里的李太白、苏学士;
元世祖也称不上什么唐明皇、宋仁宗。
再后来,赵孟頫50岁,管夫人也已过不惑之年,
玉貌一衰难再好,
情绪上的情投意合、艺术上的同生共长,生活中的优渥富余,
让他想到了,苏东坡的暮雪、王献之的桃叶(妾名),
他也想像当年的司马相如一样——纳妾。
老婆管道升听了这个事,看看镜中穿金戴银的自己,
又打量打量穿绸裹缎儿的赵子昂啥也没说
白发对黄花、老夫不雅观徐娘,有啥说的。
老娘和你一起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隐士海,
如今远走他乡,末了你说:要换人。
她没作声,不提离婚分家,也没吊颈摔碗,
你不是想当司马相如吗?那老娘就当一次卓文君。
一篇《我侬词》不亚于当年的《白头吟》: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冲破,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我与尔生同一个衾,去世同一个椁!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生则同衾,去世则同椁”
称青春匹马归来,永白头一世夫妻。
这样的情真意切,
量他赵官家心如铁石,又如何不为之动容?
在那个男人三妻四妾是家常便饭的年代,
赵孟頫终其生平,再未提及纳妾一事。
这首词,也成为当今,夫妻死心塌地的千古金句,
后来被琼瑶写进自己的歌词里,成为永恒的经典。
情深深 雨濛濛
多少楼台烟雨中
记得当初你侬我侬
车如流水马如龙
只管狂风平地起
美人如玉剑如虹
……
每个有才华的女子,都想成为李清照、管道升,
可有多少男人,不想成为赵明诚、赵孟頫呢?
女人是幸福的,男人是幸运的。
遇上对的人,永久也不算晚。
1319年五月,管道升脚气糖尿病疾笃,自知时日无多。
他和赵子昂说,想再去看看栖贤山的山茶。
未至,客去世舟中。
赵子昂记得,那年的雨很大,
山茶花白得像雪、粉得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