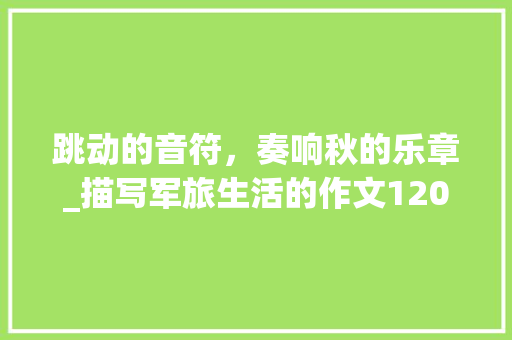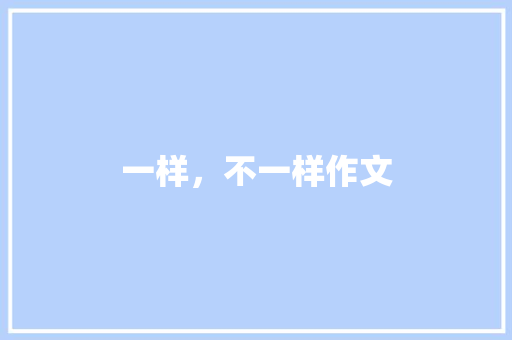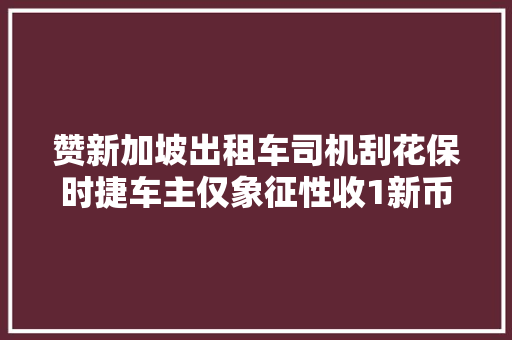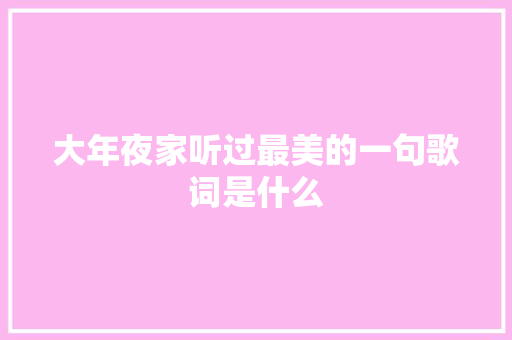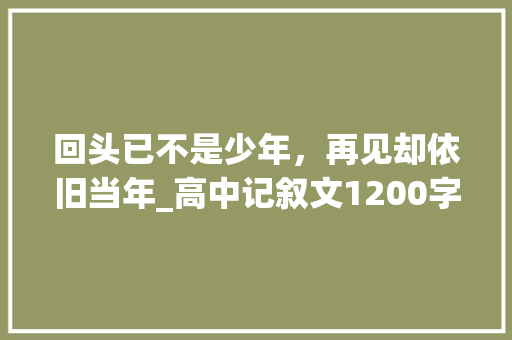1、我们被拖带的大车扔在了山顶
二十多年前的某个初冬,我、老大、年轻司机一行三人自汉中出发,驱车去往西安,清晨八点上路,车过洋县往后就有小雨落下,盘旋到地皮岭上的时候,混沌的一天雪雾,路面铺上了一尺多厚的白毯,缓缓行过西岔河,下到椒溪河河谷,却是一点雨雪都没有,到了佛坪,吃过午饭,行进到龙草坪,风雪溘然来袭,在绵长的秦岭北坡下面,四轮驱动的北京吉普再也不听使唤,先是在路上唧唧歪歪,接着干脆一口气下咽,去世在冰溜光滑油滑的陡坡半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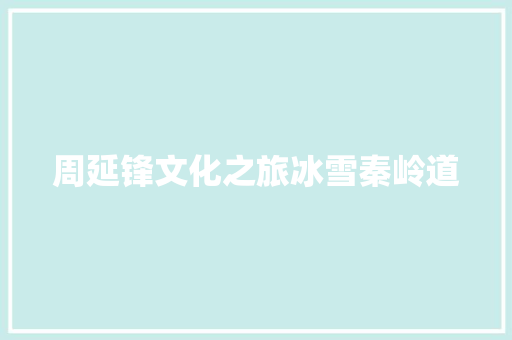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雪越下越大,满耳是雪粒落下的啸叫声,低迷、细碎、尖锐;一片冰冷的风雪声中,小车逐步被落雪覆盖,四野变得模糊起来,夜幕逐渐降临。情急之下,老大拦住了一辆过往的东风大卡车,讲好给他们一百元钱,请他们将我们连人带车一起拖带到秦岭山脊以北的板屋子镇,谁知到了山顶,那些人扔下我们,口口声声说,你们再顺道下滑二三十分钟就到板屋子了,不须要再拖了,我们将信将疑,正在犹豫的时候,他们就一溜烟跑了。
多年往后我才弄明白,他们当时扔下我们不管的缘故原由,是由于冰雪道上拖车,如果后车往前冲,或者坠崖或者侧翻打滑,链在一起的前车也会遭殃,特殊是下坡时,这种危险会更大。
懵懵懂懂,对冰雪前路一无所知的我们就此单独上路,这一去的经历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终生的影象。
2、走过冰雪阴阳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汉中去往西安的公路主干道有两条,一条是316国道,经留坝、凤县、宝鸡,路途较远,路况略好;另一条是108国道,便是我们当日所走的这条路线,经佛坪、周至到西安,听说要近几十公里,但路途比较险要。那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走这条路,市价公历十一月,根据往常的履历,陕南尚未到落雪时令,以是,我们行前未带防滑链,也未做任何可能路遇冰雪的准备。
我们被摈弃在秦岭山脊的时候,天已经完备黑了,看看腕表,已是八点多钟,万般无奈,只好顺道下滑,好在真个全是下坡,路上积雪已被压成冰溜,小车虽已失落去动力,但仍旧可以缓缓下行。
大概走了十多分钟,大概是二三十分钟,小车的灯光逐步暗淡了下去,最 后成了漆黑一团,司机喊一声“糟糕,电瓶没电了”,车子缓缓停了下来,等眼睛适应了四周的阴郁,就听见山风呜呜咽咽一直地在哭泣,神秘的、阴森森的黑影在面前跃动,阴郁中,我和老大缄默下车,一左一右傍着前灯两侧,权当是车的眼睛,就这样溜过一段陡坡,转个弯,山势变得略略平缓,路上全无冰雪,雪落下来就成了水,而水正被汽化,蒸腾浮荡,带着一些些暖意,给人一种虚幻迷蒙的觉得,走不多远,转过弯,又是一片雪窖冰天,路面反射着幽幽暗光,走在上面,东倒西歪,稍不留神,就会来个仰面朝天;就这样,走过冰路走雾路,走过雾路走冰路,不知不觉,冰雾交替的阴阳路不知走了几重,一道山弯转过,溘然是一段电光火石的长坡横在面前。
3、幻影重重
那一夜,我们默默行走在山路上,不知走了多久,没有一辆车跟随,没有一辆车超越,没有一辆车经由。孤单、无力又无措的觉得跬步不离,路上行走着的彷佛只是个皮囊和空壳,灵魂就在头顶上盘旋着,默默看着自己,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空茫、虚幻又恐怖的觉得。
就在我们茫然赶路的时候,一道山弯转过,一段电光火石的陡峭长坡溘然展现在面前:通明的灯火映照下,一溜儿几辆大卡车正在冰壳上挣扎,发动机的轰鸣声,人们的呼喊声,山风推着车辆东倒西歪的哧溜声,狭窄的路面无法承受挤压,路的转弯处,两辆相向而行的大车叠加在一起,正在一寸一寸向路边滑去。
“危险!”我大喊一声,但在冰冷的深山之夜,这一声叫喊竟不如蚊蝇的嗡嗡,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把稳,我们的小车这时开始在冰路上打起摆子,年轻司机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朝路边的大石头努努嘴,我赶紧走过去,准备用它来垫挡车轮,就在这时,我觉得有人攉了我一把,那石头翻滚着,自已跑到了车轮底下,车趔趄一下,稳稳地停在了路边。
多年以来,我对这个细节百思无解,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了我一把,也不知道那块石头为什么会自己走到车轮底下。只是那时,当我转身站稳时,那两辆挤在一起的大卡车已经轰轰隆隆从山路上跌落下去,深不见底的山谷响起一阵又一阵咕噜声,像是嗟叹,又像是欢呼,紧接着,便是砰砰訇訇的爆裂声,火光冲天而起,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略显稚嫩的年轻嗓音,凄厉地狂叫:老天爷,我还没结过婚呀!
4、诡异的惨祸
蜀道难,难于上上苍。从古至今,有多少怨魂丧生在这条路上?公路开通以来,最险确当数316国道地皮岭段:在陡峭的崖壁上凿出的公路环抱褒河水库下行,不到十公里山路垂直落差一千多米,站在山顶俯瞰下去,深幽幽的水面就像妖怪的眼睛。这段路呑噬了多少生命?大概没人说得清楚。隔三差五,人们从成片漂浮在水面的杂物就可以推知,又有若何的车辆消逝在了水面之下。
在那鬼魅般的夜晚,秦岭深处的冰雪陡坡上,我眼睁睁看着两辆大卡车坠入深谷爆炸动怒,嗡一下,脑袋一片空缺,良久,有人在后颈拍了一把,是老大,“你发啥呆啊?”他问我“那两个大车掉下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喉咙有点哽咽。
“什么大车啊?在哪?”他又问。
“在那”,我抬手指指下方,顺手再看过去,却是黑蒙蒙一片,刚刚还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已是了无踪影,面前唯有山风依然在呼啸。难道那统统都是幻觉?转身看看,刚刚还在路上的车辆全部不见了,消逝了,无影无踪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浑身的汗毛不由得一根一根立了起来。
“快走吧”,老大彷佛对我看到的这些一无所知,他拉了我一把,我随着他木然地回到车旁,借着司机闪动的烟火,瞥见车轮底下那块大石头确确实实稳稳地垫着,心才逐步回到胸腔里来。
三个人都坐在了车上,冷风像一把把剔骨钢刀直插进来。“走吧,总不能窝在这里等去世呀”,老大说,我们随即准备动身,面前的路面“唰”一下又一次通亮起来,这回,我们三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辆加长东风在冰溜上挣扎着停了下来,胡子拉茬的老司机跳下车来,径直走过来,走到我们车前,一弯腰就抱起了车轮下的石块,返身走了回去,就在这时,车里的老大重重地咳了一声,顷刻间,所有的光芒溘然消逝了,面前依然是一团看不透的黑雾,紧随着,咔咔嚓嚓的车辆滑动声伴随非常凄厉的一声惨叫陡然腾起,在无边无涯的阴郁中久久回荡。
“啊---”
5、道班夜话
我已记不清我们三个人是若何跌跌撞撞走到公路道班的小院里的,走了多久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斗室子的门是被我们擂开的,颤颤嗦嗦,两个工人把我们让进了室内,阴暗的灯光下,他们惊异地打量着我们,过了良久,年轻的那个嗨一声,大喊道:真是三个活人呀!
在温暖的屋子里,我一点一点回过神来,满头长发上的冰凌子开始融化。回忆起来,那时的我们一定够吓人的。我们浑身尽可能包裹着统统可以保暖的东西,胸前身后斜挎着能够随身带走的物件,手里紧攥着胡乱捡来的树棍,面无红色,魂游身外,猛然一见,实实在在说不清是人是鬼是怪是匪。
两个工人十分友善,很快给我们端来了茶水。滚烫的热杯子拿在手里,坐在温暖的火炕上,觉得很快就鲜活起来。
“你们怕是遇见鬼了”
年长的工人开了口,从他的陈说中,我们知道了这一晚离奇经历后面的分缘,说的便是在那个地方,几年前,确确实实有个老司机在冰雪路上垫石头的时候被自己的大车压去世了,而大车坠崖落坡爆炸动怒也曾确确实实发生过。更离奇的是,打那往后,午夜经由那里的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目睹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而那个被压去世的司机,也会常常以意想不到的办法给遇险的车辆以帮助。
不久,阵阵鸡鸣传来,一点一点,天亮了,出门去看,公路从一大片平缓的山坡蜿蜒下行,道路两旁,散落着高矮不等错落有致的一些建筑,举目远眺,满天下的纯白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板屋子到了。
6、板屋子
板屋子是秦岭深山的一座小镇,建在半山腰,行政区划从属周至县。说是小镇,实在不过四五家住户,但有供销互助社,互助社院子里有小旅店,镇上还有小饭铺,有个小小的汽车修理厂,实在也就只能修胎补气而已,连给电瓶充电的条件都没有。这里的房屋大多建在国道两旁,靠路的一壁墙体高大厚实,门窗局促,彷佛还有点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式建筑的风格。
上午十点,老大由于重任在肩,就坐过往班车去西安了,留下我和司机在板屋子,说好他到西安后就打电话联系佛坪的朋友,请履历丰富的朋友帮忙我们拖运车辆到板屋子,再想办法修睦,开到西安会合。
小饭铺是两个中年男人打理,上午十点多才开门,鞋子趿拉着,蓬乱的长发看样子半年前洗过一回。这两人一个抠着鼻孔,骂骂咧咧出去点火,一个搂着裤腰,边系裤带边挠痒痒,哼哼哈哈过来和面,说是本日供应油泼面,宽面扯到锅里,捞到碗里,撮一把干辣面细蒜末,“嗤啦”半勺滚油一浇,不把人喷鼻香去世,就把鬼喷鼻香活,“僚的太太”。
这样的大师傅主厨,他们做的东西怎么下咽?看来,板屋子的第一顿饭只好去供销社买饼干了。
供销社在小镇中间,小门进去便是值班室,值班室外间是小商店,值班的中年妇女在炭火盆子旁烤火,空气中有烤土豆的喷鼻香味,一高一矮两个年轻女子坐在里间的火炕上吃着土豆说闲话。高个女子眉目俊秀,笑模笑样,矮个女子玲珑利飒,小家碧玉,见有生人进来,两个女子边打呼唤边下炕,我们的年轻司机顺手捏了几片饼干让她们,她们不要,却搭起话来,山里山外,没说几句,就有了嘻嘻嘻的笑声。
十一点多,太阳出来了,瓷白瓷白的一坨冰疙瘩在空中楦着,出门去看,群山万壑银装素裹,满眼被冻结的景象,空寂中透出一种肃穆与肃杀。隔了一会,YY叉叉的树枝上飞来几只喜鹊,嘎嘎声冲破了四周的寂静。
站在板屋子路边的沟坎上,群山彷佛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
7、黑女子,瘦女子
直到傍晚,佛坪的朋友了无踪影。山风一起,浮雪开始在林莽的边缘呼号奔忙,风卷着雪粒沿着山脊和沟谷滚下去又滑回来,一波一波,荡入杳远的无际涯界。
晩饭在供销社小灶搭伙,高个女孩的手艺,红苕玉米珍稀饭,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帅司机已经嚷嚷着给两个女孩先容工具,说是汉中人,和我和他一样平常高,一样平常帅。
我和司机都是北方人,都在一米七五以上,算得上高个子。我一点都不帅,但多年前有个叫花子说过我帅,由于我给了他两块钱。司机确实很帅,裤子前后的熨烫线直溜得能裁纸剪布。
困在山上的车怎么办?
“等,反正我们也没办法”,司机说。
这一夜,我们就住在供销社的小招待所里。我们的帅小伙子彷佛已经忘却了曾经的历险,忘却了车辆还在山脊的冰雪路上,他给两个女孩取了两个名号,高个子叫“黑女子”,矮个子叫“瘦女子”。黑女子虽说姣好,但在山窝窝里烤火,烟熏火燎的,脸有点黑,矮女子精透伶俐,但一蹦一蹦,轻飘飘的,显得过于憔悴。高女子是“接班女”,便是接了或父或母的班,成了领人为的“公家人”,矮女子是高女子的同学,闲着没事来山里玩。这一夜就在闲扯'黑女子''瘦女子'的话语中沉入了梦乡。
板屋子的第二天艳阳高照,我们仍旧在等佛坪来的接济,帅小伙已经坐到了黑女子瘦女子的火炕上打起扑克来。午饭过后,供销社的男主任回来了,胡子拉茬,肩上扛着一只杂草色的小麂子,得知我们的情形后,二话没说就出去了,隔不多久,领着一位精瘦的半大老头目进来,说是这老人开车走冰雪路招招过硬事事能行。
“你们给多少钱?”
“多点少点没紧要,只要安全弄下来”,司机说。
“一百五”
“一百五就一百五”,司机跟了句:“大概车被佛坪人拖走了,你们跑了空趟不给钱”。
“行”老人很爽快,转身就走了。
8、老林子里的黑熊己经冬眠
艳阳高照,整整一个下午,在板屋子街后的高坎上,我把自己完备融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环抱中,心境变得澄澈起来,彷佛自己一贯便是这里的一位山民。不知不觉,大雪封山的经历深深嵌入了我的灵瑰。多年往后,我码下过这样一段笔墨:
老林子里的黑熊已经冬眠
大雪封山
几只喜鹊在丫叉的枝头
戛戛
它们是这个时令的主人
结冰的小河
保持着涌流的姿态
仿佛等待
有谁来把群山唤醒
只是一霎
风呜呜咽咽超越山脊
枯瘦的草木抓不住
风跌落在深谷
愣怔间
又滑了回去
哎嗨嗨——
站在屋前大喊一声
等半天
没有一丝覆信
满天下的纯白刺痛了双眸
抓几粒苞米
伸开手
静等着山鸟们飞来
它们成了你
日复一日的伴侣
这天傍晩,老人将我们的北京吉普缓缓滑进了小镇的汽修厂,粗略检讨一下,水箱上半部冻裂了,电瓶没电了,化油器调一下就好,其它并无大碍。师傅们说,只要电瓶能有一点电,或者有人帮忙打火,或者能推着发动起来,车实在可以开走,只是途中须要不断加水,但前几点都做不到,还是走不了。
当天晚上,帅小伙说他感冒了,第二天一早,又觉得自己发热了,商量的结果是,电瓶拆下来,我带上,坐班车去周至县城充电,充好电再回山里来。
9、山祭厚畛子
这已经是在板屋子的第三个日出了,太阳非常通亮,路上的冰雪已经融化,干爽的水泥路上,班车走得轻松清闲,在野狐崖,一辆橘黄色加终年夜货车斜躺在河道,川字牌照,显示着几天前那场大雪的威力。在厚畛子出口,一辆五菱红光与小四轮搂肩搭背僵在那里,车体上彷佛有一些血迹,车上的人正在吵架。到了虎豹沟沟口,汉运司的一辆绿皮大客车停靠在崖底,头顶镶着大约有三五百斤的一块麻光石。进了虎豹沟,阴风扑来,两山来峙,河道逐步逼仄起来,板屋子那条小渠沟已经变成了彭湃的河水,河床逐渐低落下去,公路间隔河床抬升到了上百米,路在崖上,千回百折,到马召镇出山口,一个大弯,一边傍崖,一边临河,峭壁陡直,河床间隔路面已有两三百米,路上积雪浮冰,司机停车,全车搭客下车,靠山缓行,职员安全集结,然后车辆通过。车行其上的时侯,只管有防滑链唰唰作响,但是仍旧打滑。司机老道,边滑边走,看得民气惊胆颤,大气莫出,脚底生凉,双腿簌簌颤动。
周至县城一行还算顺利,只是电瓶充电颇费韶光,越日九点多钟,我坐上了返回山里的班车。
这趟车逆水爬坡,走得却是顺风顺水,几十公里险道走过,到厚畛子路口,正遇上一队人马披麻戴孝吹奏乐打在祭拜,下车一问,原来正是昨天失事的罹难者家人在拜山祭路。
厚畛子路口是108国道秦岭山区的一个主要岔路口,自这里入山,可去往佛坪老县城。那座老县城十分险远,交通极为不便,民国期间曾有山匪长年盘踞。有趣的是,强盗头目自任县长,竟然把那里管理得很好,后来强盗清剿了,住户逐渐迁走了,就逐步荒弃了。
自厚畛子入山,另一条路通往太白山主峰及大爷海小爷海等天然景区,但坡陡路狭,地质条件繁芜,野生动物活动频繁,迷花倚树,熊咆龙吟,常有游客在这一带神秘失落踪。
厚畛子路口也是108国道秦岭山区段的主要节点。这里往下即进入黑河河谷的盘山险道,这里往上,经野狐崖,直到板屋子,路途相对较为安全。正好是这个道路节点,却也每每是事件高发的地点。
班车司机虔诚而迷信,搭客也以这一带山民居多,大家惺惺相惜,气氛有些压抑。停车,等待,看那祭拜军队,彷佛也是附近山民,几位女子哭哭啼啼,嘴里陈说着日子的困难,说得多了,有人就骂起山神路神来:不要脸神呀,你要命,咋要的全是青壮的命,这可叫人怎么活呀。头带道巾的一位老者焚了喷鼻香蜡纸表,嘴里念念有词。二十多分钟,一阵鞭炮响过,硝烟弥漫,班车连续赶路。
到板屋子大约下午三点,那时司机帅小伙正一个人黑着脸蹲在值班室吸烟,瞥见我回来了,猛地跳起来,喊了一声“走”。
10、惊魂虎豹沟
我们结账离开的时候,黑女子表情繁芜地望了一眼,低头走开了。司机一起跃马扬鞭,看看过了野狐崖,过了厚畛子口,进了虎豹沟,转过一道弯,阴坡处,一大一小两辆车都头破脸瘪,虎着脸对望着,听一伙人在辩是非,辩着辩着就吵了起来,一吵架,就堵车。我们车体小,寻机穿过去,正要走,一个四十多岁的灰脸男递根烟过来,要搭车,聊了几句,知道是要去周至县城找交警处理事件的。
连续前行,河道已降至路面以下二十多米,二档行进,转三档,一道急弯转至阴坡,车开始在路面上玩飘移,十米,二十米,只一瞬间,就在即将在坠崖的一霎时,对面一辆东风卡车前保险轻轻拉住了北京吉普,唰啦一声,一百八十度,小车牢牢依傍着大车停在了路面上。
足有三分钟呆愣,司机帅小伙溘然趴在方向盘上“哇”一声大哭起来,再看身后,那个搭车的中年男子跳下车一蹦一歪往回跑去,边跑边喊见鬼了,见鬼了。
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刹,你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经结束。本能,唯有本能才是任何事件中人类最真实的行为,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年事,受过什么教诲,是男是女。事先的任何想定和预案都没有什么用。
命运完备在于有时的机缘,或者说,命在老天。
这个惊魂不定的傍晚,我们掏光了身上的所有泉币,连备胎都卸给对方往后,才困难的离开了那里。从此一档行进,走走停停,融雪加水,大约凌晨三点,终于走出了山口,听见了马召镇的鸡叫,瞥见了模糊约约的灯光。
(全文完)
【作者简介】周延锋,男,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规复高考首届大学生,多年从亊干部教诲培训事情,业余爱好书法,喜好奇石收藏,偶尔写写文章。
审核:田也,作者:周延锋,责编:楠阳,序号:728
汉中市赤土岭文化互换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年夜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