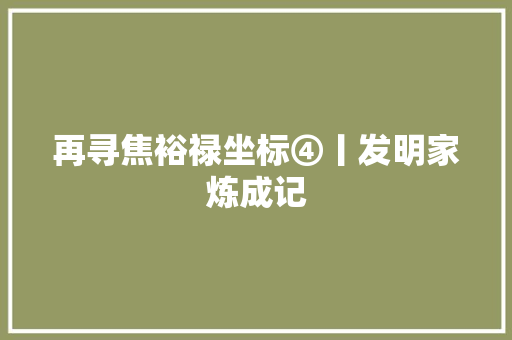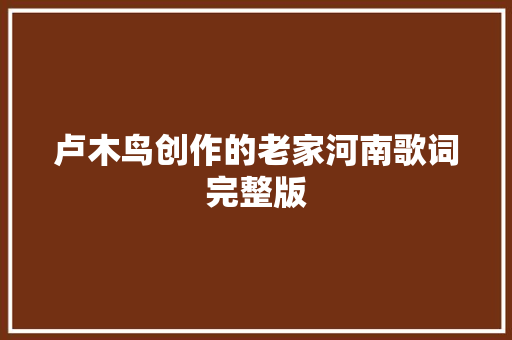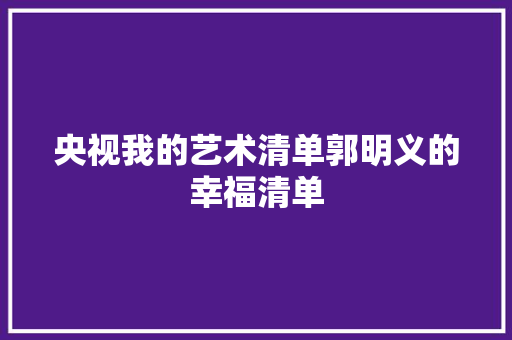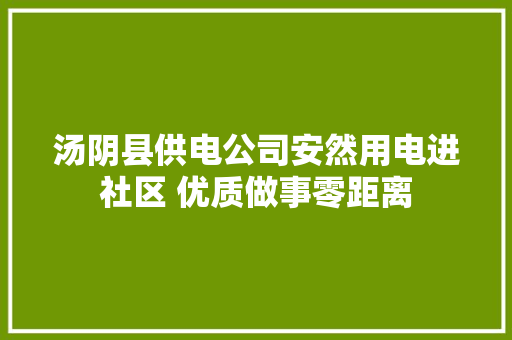习近平同道殷切哀求党员干部,要“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实正派的党员,做一个可靠、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焦裕禄干部学院内的焦裕禄塑像新华社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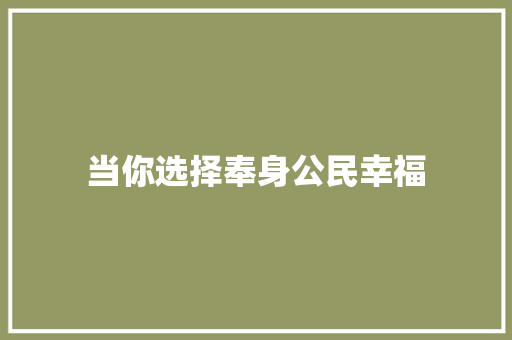
仰望历史天空,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三位在事情岗位上殉职的党员模范,像三颗光华残酷的星,格外耀人眼目。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逢党的华诞,追寻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三颗公民仰望的星,如何修睦为官之德的新时期之问,犹如稍纵即逝,洞穿历史,贯通未来。
源于“小村落总理”的情怀
在渤海根据地中央山东省惠民县,1947年底从油坊张村落出发的南下干部大队,是揭开山东10万干部南下序幕的首发阵容。孟冬将尽、寒月在望,焦裕禄和他的战友在这所准军事化革命熔炉加钢淬火3个月,斗志昂扬随改称淮河大队的军旅出征。
战斗行军,一起艰辛自不待言。为防止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常日安排夜间行军,但敌机投下的照明弹亮如日间,炸弹时常在行军队伍附近爆炸。焦裕禄所在的二班,有王殿英、姚采侠、蒋敏等好几个“花木兰”,大家背着背包、米袋,有的还携枪带弹,足有几十斤重。每天行军近百里,班里的战友脚上都打了泡。焦裕禄抢着帮大家背背包,最多时一人背了4个,还跑前跑后搞宣扬煽惑。长途行军呆板乏味,焦裕禄诙谐风趣的话语,常使大家愉快一笑,忘怀了行军疲倦;他张口就来的顺口溜,上口易记好懂,成了行进中给大家加油的好形式。焦裕禄带“铜音儿”的金嗓子,领唱《打得好》等行列步队歌曲,使全队激情迸发,士气大增。一到宿营地,别人累得像一摊泥,焦裕禄却乐此不疲忙着抱干草、打地铺,给班里战友烧水洗脚,直到全班安然就寝。
南下路上最扣民气弦的,还是在敌占区强行通过陇海铁路。午夜时分,天降大雪。队员们快速向铁路线机动,警卫战士卧在铁路两侧雪地掩护。女队员王殿英几次滑入雪坑,均被焦裕禄拉出。在野鸡岗车站附近,女队员蒋敏溘然掉进雪坑不见踪影。焦裕禄扔掉背包,迅速将人救出。在他悉心关照下,二班无一人掉队。全队雪中疾进数小时,终于在拂晓时分到达宿营地。
累并快乐着,雏鹰展翅的焦裕禄南下路上收成了分外幸福。
焦裕禄在兰考。资料图片
1948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由淮河大队排演、焦裕禄饰演男主角的歌剧《血泪仇》,在豫皖苏边区驻地鄢陵县北彪岗村落上演。边区和军区领导同道,同临近几村落数千名群众一起不雅观看演出。大幕开启处,浸透着苦难与悲情的歌声,与当天上午枪决民愤很大的国民党乡公所无赖的枪声奇妙领悟,打开了十里八乡积蓄已久火山的出口。沉浸剧中的不雅观众,怒气冲天向舞台上的恶霸地主扔石头,有个眼里冒火的战士还举起了枪,被眼疾手快的指挥员按住。世代在地下奔突冲撞的血海深仇,熔岩般呼啸着喷涌而出,像是要焚毁人间间统统丑恶与不平,成为轰轰烈烈开展的土改建政的先声。
演出结束后,豫皖苏边区党委副布告章蕴上台讲话。她感谢淮河大队带来这么一台好戏,宣告经报上级批准,原定开进大别山的淮河大队,根据须要留下来,和当地公民一道,剿匪反霸,开展土改,推进地方政权培植……
始于山东油坊张村落的南下,在河南彪岗村落戛然而止。焦裕禄及其战友的勇毅和才华,改变了自己和一个群体的人生轨迹。后来,人们回望焦裕禄及其战友且歌且行的南下征程,创造这个展示焦裕禄早期做事"大众年夜众激情亲切和才能的平台,是透视模范竭诚为民生平和焦裕禄精神缘起的窗口。
《血泪仇》使焦裕禄与黄河中下贱交界处结缘后,1948年2月,他作为区事情队辅导员,带领20多名干部来到敌我拉锯区尉氏县彭店区(今鄢陵县彭店乡)剿匪反霸,弹压了策划纵火对抗土改的恶霸地主朱德林,组织民兵两度挫败鄢陵县伪保安大队长洪启龙率数百匪兵来袭,把彭店区的土改搞得风生水起。任尉氏县大营区区长后,他在“大营九岗十八洼,洼洼里头有盗贼”的强盗窝,带领民兵“三擒两纵黄老三”,粉碎了强盗里应外合暴乱的阴谋,使强盗盘踞多年一塌糊涂的大营晴了天。当年11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彭店区支前民工大队长,率领2400多名支前健儿顶风冒雪挺进淮海域场,圆满完成了运送面粉、转移伤员等任务。
1953年6月,焦裕禄由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布告,选调苏联援建重点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今中信重工机器株式会社),在幕天席地中带领工人筑路建厂,再度显示了越繁忙便越充足、越奋斗便越快乐的禀赋。
1962年6月,焦裕禄调任尉氏县委布告处布告,当年12月受命赴重灾区兰考主持县委事情,后任县委布告,使他渴望为"大众做事的激情亲切,在天高地阔中得以充分开释。善良的天性一旦融入党的宗旨,急速便光华四射。
我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出身的风雨进程》时理解到,焦裕禄发小和同学李安祥曾回顾,焦裕禄从小朦胧孕育的空想,是终年夜后成为一个识字断文、诸事皆通、德高望重,能总理村落中红白喜事,为百姓操劳和造福乡里的人。
“耕读之外以行仁为务。”源于族谱的家训,是编织和放飞焦裕禄人生梦想的第一双手,“小村落总理”成为他生命之树最早开出的空想之花。焦裕禄南下后转战大河两岸16年,无论在哪里奋斗进取,都一以贯之保持了气势如虹南下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情怀,都依稀可见南下路上他那永不知疲倦的身影。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精良人物高尚原生志趣,经革命斗争实践提纯升华并与党的初心相契合,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倍增和放大效应,在孔繁森和郑培民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一次,孔繁森下乡听见一位晚上睡觉时磨牙,便问他到藏区几年了?得知这位入藏五年常在牧区吃牛羊肉,根据高原肉难以煮熟和常吃风干生肉肠道易生蛔虫的履历,孔繁森从自备小药箱里拿出治蛔虫的药,服用后很快打下了虫子。
1994年藏历新年前,《西藏青年报》张焰到阿里札达采访,孔繁森给他派了一辆车况较好的车保障。傍晚,孔繁森给札达打电话,得知张焰尚未到达,便判断车在路上出了状况,急忙折衷驻军前往搜救,果真在路上创造了侧翻的汽车。张焰冲动地说,要不是孔布告及时派人营救,我们几个肯定要葬身雪原!
哪里最艰巨,就先到哪里去;哪里最贫穷,就到哪里去蹲点。工人后代郑培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布告任上,爬过湘西最难爬的山,走过湘西最难走的路,去过湘西最穷的村落庄,住过湘西最穷的人家。上任伊始,他就问:“全州哪个村落最穷?”随后径赴三面峭壁一壁山的叭仁(苗语“山顶”)村落,从乡里徒步4小时,手脚并用爬上这个只有乡干部到过、累去世人也能吓去世人的山头。他骤然病逝后被称为“三民布告”(爱民、亲民、齐心专心为民),是百姓对有着先忧后乐情怀公民公仆的最高褒奖。
“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公民”
1988年10月,山东聊城行署副专员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前,给八秩晋七的母亲梳完头,脸贴着老人耳边颤声说:“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三儿啊,咱不去弗成吗?”年迈的母亲抚着他的头问。
“弗成啊,娘,咱是党的人,咱得给公家办事啊。”
“那就去吧,娘知道公家的事误了弗成。多带些衣裳、干粮,路上别喝凉水……”
孔繁森长跪不起,流着泪给母亲磕完头,一步三转头走了。
这一幕,曾经使多少人潸然泪下!
担心儿子喝凉水的老母亲哪里知道,儿子要重返的西藏高原地广人稀,汽车跑半天也不见人烟,沿途既无山泉,更无水井,如诗如画的湖泊都是盐湖和半盐湖,夏天只能喝冰雪融水,冬天只能化冰块、吃雪团!
1944年7月,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孔繁森降生京杭大运河边五里墩村落(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时,日寇履行的细菌战和旱灾、蝗灾,使周遭百里成为无人区。那年母亲已43岁了,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搂着大孙子,那种艰辛和不易,刀子样刻进孔繁森的苦难影象。家贫出孝子。孔繁森特殊疼爱一辈子茹苦含辛的母亲,当了领导也常忙里偷闲回家,给老人端水送饭,梳头、洗脸、洗脚、剪指甲,用地排车拉着她看花灯,逛小吃摊……
作为孔子第74代孙,孔繁森何尝不熟稔“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但他懂得,当党和公民的奇迹与个人家庭亲情难以得兼时,党员领导干部应该若何对待、若何处理、若何选择。
孔繁森(右)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资料图片
孔繁森首次援藏是1979年,他任聊城市委宣扬部副部长,正是人生爬坡最吃劲儿确当口:父亲70岁,母亲78岁,3个孩子分别是8岁、6岁、2岁,除他之外,一家三代户口都在屯子。组织上动员援藏,他报了名。人们迷惑,他说:“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你也困难,我也困难。但援藏总得有人去吧?”
孔繁森原拟任日喀则地委宣扬部副部长。可报到后,领导看到他身体和精神俱佳,又改派他任边疆县岗巴县委副布告。孔繁森即刻履新。日喀则市区海拔3836米,岗巴海拔4700米,含氧量不敷内地的50%,比日喀则低15%旁边。孔繁森走上了更为艰巨的高原,他的思想也升华到新的境界。这一去,便是3年。
1988年秋,中组部确定从山东选一名40岁旁边、有援藏履历的副厅级干部带队入藏,孔繁森进入视线。当时,他87岁的老母已瘫痪在床多年,首次援藏坠马使他落下了颅脑伤。搜聚他见地时,他再次选择服从,但迟迟未见告家人。临行前,孔繁森破天荒领着妻子儿女到北京游览,返回时见告妻子自己将再度援藏。妻子明白了他带家人旅游的苦心,泪水扑簌簌滚落下来。
再上高原,孔繁森任拉萨市副市长。勤奋事情之余,他思念白发亲娘和妻子儿女,每次给妻子打电话都泪流满面。然而,肩负的义务与任务,当年坠马后藏族父老的救命之恩,使他已离不开这爿高天厚土。至真至纯的孝老爱亲之情,已然拓展升华为情系高原、悲悯苍生的大义仁心。他说:“西藏的老人便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便是我的孩子,西藏的地皮便是我的家乡!
”
拉萨市有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孔繁森去过48所。隆冬时节,孔繁森顶着寒风来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看到琼宗老人的鞋子破了,脚冻得通红,心疼地解开棉衣给他暖脚。第二天,孔繁森又给老人捎去妻子做的一双新棉鞋,此后又掏钱给这个敬老院的老人买了收音机送去。为孔繁森送行时,旺姆老人冲动地对他说:“还是新中国好哇,假如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本布拉’(藏语‘大官’),我们连见都见不到啊!
”
孔繁森常常吟唱“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他曾在济南军区总医院服役,粗通医学,外出总是自费买些常用药装在药箱里,送给缺医少药的藏族群众。一次,孔繁森去拉萨尼木县敬老院慰问,恰遇一位老人被浓痰堵住气管,情形危急。他果断拔下听诊器胶管,接连给老人吸了几口痰,使他转危为安。像这样凡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孔繁森并非偶尔为之。岗巴县昌隆乡的仁青就永生难忘,1979年他刚两岁时,是孔繁森吸出了堵在他气管里的痰,才使他分开了生命危险。
二次援藏期满,孔繁森该回家与亲人团圆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布告热地却问他,能不能留下来,到阿里地区事情一段韶光?孔繁森意识到这是党的召唤,遂当仁不让走向“生命禁区”,以两次援藏、一次延期的决议,把人生最好的10年献给高原。
孔繁森在拉萨市指挥抗震救灾时,在直孔区羊日岗乡齐马卡村落创造了3名失落去父母的孤儿,哀求村落里安置好。可后来他两次到该村落,创造3个孩子仍在流浪。鉴于村落里短缺安置条件,孔繁森将3个孩子送到县中央小学包吃、包住,自己每月给学校300元作为孩子的零费钱。几个月后,孩子不适应学校环境,闹着退学。孔繁森便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给他们洗衣、做饭,教他们读书认字,孩子病了背他们去医院就诊。拉萨市长洛桑顿珠见他包袱太重,领走了大孩子曲尼。后来,噶尔小学有个老师要代孔繁森收养个孩子。他感念老师古道热肠,又担心兄妹俩分开会在心里留下阴影,婉言回绝了。在孔繁森和大家关怀教诲下,孤儿们康健发展,贡桑后来还考上了南京大学。
孔繁森在阿里月人为加援藏补贴近千元,由于赡养孩子和救助群众,手头竟然十分窘迫,曾化名“洛珠”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卖过3次血,每次300cc,得营养费900元。他逝世后,人们从他遗物中仅找到8元6角钱。这些钱按时价只能选择买一个半鸡蛋、1两菠菜、7两大白菜。泪眼婆娑中,人们忆起他给困难群众送衣送钱,雪天看到一位冻得瑟瑟颤动的老阿妈,回车里脱下毛衣毛裤送给她的往事,不禁想起下乡常“丢”衣服的焦裕禄。
焦裕禄病逝后,亲人们从哭着找到家里来的农人身上,看到了他下乡“丟”的衣服。他踏雪走进城关公社梁孙庄梁俊才家,对生病卧床的老人动情说“我是您的儿子”的经典画面,曾经使多少人热泪涟涟,又唤起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初心!
眼下,对藏族公民解衣推食的孔繁森,不正是西藏高原的焦裕禄吗?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公民。”习近平总布告曾把孔繁森说的这句话,誉为“孔繁森的境界感”,作为共产党人该当具备的五种崇高情绪之一。
孔繁森在部队开展的学雷锋、学焦裕禄活动中,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他照料过的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徐诚,当年与马海德同在延安八路军总医院救去世扶伤,多次以自己的O型血将危重伤员从去世亡线上拉回来,堪称他的精神教母。雷锋、焦裕禄精神化育,老前辈言传身教,是孔繁森的爱臻于化境的催化剂。他被誉为“九十年代的焦裕禄”,其来有自。
当捐躯成为壮丽的涅槃
春到湘西,自治州州委布告郑培民,高挽着裤管,同干部群众一起下田,铆在一线实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能。
对付湘西自治州这个常闹春荒的穷苦地区来说,推广这项新技能,是办理全区群众用饭问题的关键一招。新法植苗好比土里绣花,要在田中豆腐块大小的方格周围摆两株苗。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的郑培民坚持科技领先,亲力亲为示范引路。可整天把腰弯成一张弓,年轻后生都受不了。那时,1992年的日历已翻过了两个月,已经“奔五”的郑培民身体还有些胖。可他像是忘了自己的年纪,整天跟后生们摽在山上。连续几天弯腰弓背,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3米多高的田坎,当场呕吐并虚脱。送医院检讨,确诊为脑震荡。州委布告下田摔成脑震荡,值吗?
答案来了:这一年年底,湘西粮食开始实现自给自足。
郑培民下乡参加劳动。资料图片
1943年出生的郑培民,从工业部门转上农业战线后,官声颇佳。1990年5月,他从湘潭地委布告调任现职,曾引起预测。在湖南,湘潭与湘西虽一字之差,却有寰宇之别。当时,湘西是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边远穷苦地区,有150多万人生活在穷苦线以下。郑培民这次调动,是为了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步伐,还是培养性互换?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着,不过多数人认为,郑培民易地为官,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
“我们当时还担心培民同道心里有想法,没想到他二话没说就接管了组织的安排。”时任湖南省委布告熊清泉找郑培民发言后,满脸都是掩不住的欣慰。郑培民咋表态呢?他在自治州干部大会上当众撂下两句话:“来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专一苦干!
”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大家一下子喜好上了这个新来的州委布告。知根知底的事情职员心却提溜起来:郑布告这个“冒死三郎”,做“州官”还在汽车里塞条被子打着滚过夜,他跟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嘎亲”熟年头了,来湘西扛把子,能顶得住吗?
这种担心,被郑培民种玉米跌下田坎摔成脑震荡的惊险所印证,也被他当了省委副布告在常德指挥抗洪,同干部群众一起用沙袋堵决口的实干唤起,直到2002年3月11日,郑培民奉调在京干大活,因劳累过度以身殉职,才画上沉重的句号。
有这样描述郑培民:他在湘西事情两年多韶光,跑遍了全州218个州里,住过30多个州里。撤除在省里开会、办公的韶光,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是一个没有机会喘息的数字。
2019年9月25日,在庆祝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同时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三位为党的奇迹奋进不息的模范,都是在和平年月因积劳成疾或意外事件在事情岗位殉职,都是在人生最大有可为的阶段英年早逝,都是在为公民福祉奔波的路上骤然离世——
42岁的焦裕禄倒在带领公民管理“三害”的路上;
50岁的孔繁森倒在赴边城办理制约阿里发展问题的路上;
59岁的郑培民倒在参加预备党的十六大干部稽核路上。
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义务,同一个“最美奋斗者”的姿态。他们的捐躯,奏响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公仆颂,演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党的先锋战士为公民大胆献身的壮丽涅槃。
焦裕禄是三位模范中唯一经历过武装攫取政权和“进城”双重磨练的第一代执政人。作为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幸存者,他对打江山的不易和珍惜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有着更深的理解,对尽快除害安民有着更强的政治自觉。日甚一日的肝病使他腹部像是“杵着一只生红薯”,乃至不得不用硬物抵住肝部缓解痛楚。但为了早日让兰考公民过上好日子,他以杜鹃啼血的殉道精神背着去世神冲刺,把负重前行的兰考岁月,演绎成一曲砥节奉公、舍生济民的大义之歌。焦裕禄临终前向组织提出埋骨兰考沙丘,看着战友带领公民把沙丘治好的遗嘱,成为那个时期共产党人生能舍己、去世不还家伟大捐躯精神的标志性场景。
孔繁森衔命西行时,新中国成立已30年,西藏和平解放已28年,但捐躯仍未远去:反分裂斗争誓不两立,“生命禁区”潜藏康健杀手,“道路陷阱”遍布雪域绝壁……告别故里前,他请人手书“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去世不回籍”条幅;到西藏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铿锵誓言。
“最痛楚的是思念亲人的时候,最危险的是在险象环生的路上。”孔繁森三次高原历险,两次都在路上与去世神擦肩而过。
1980年5月,孔繁森在岗巴县察看雪灾,归途中不慎坠马,一只脚挂在马镫子上被拖出几十米远,头部被撞伤,是老乡用门板抬着他跋涉30多里送到县医院,他晕厥3天3夜才醒过来。
1989年11月14昼夜,孔繁森乘车去山南开会时与拖沓机相撞,甩到车外造成颅骨骨折和严重脑震荡,一小时吐血7次,有几个山东老乡乃至备了将他尸首运回老家的冷藏车。这次车祸给他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右眼成像重影、颈椎损伤等终生残疾。
孔繁森纪念馆陈设一日记本,上有孔繁森1994年2月26日凌晨,在海拔近6000公尺处写给事情职员梁福兴的遗言:“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觉。我有一事相托:万一我发生了不幸,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纪念馆老馆长高杉见告我,当时,阿里高原遭受50年不遇狂风雪,孔繁森为救灾奔波16个昼夜后胸闷气短。高原生活履历和医学知识使他作了最坏的打算。这个真实记录孔繁森危境心曲的日记本,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跻身100件齐鲁宝贝之列。
山东省省立医院和西藏军区总医院影像检讨结果表明,时年47岁的孔繁森的大脑,已萎缩成60岁老人的状态;因患有高原性心脏病导致代偿性肥大,他的心脏比正凡人大了三分之一!
孔繁森猝然去世,给阿里公民带来的哀恸,仅次于活佛圆寂,他的照片被虔诚地供奉在藏族百姓的佛堂和神圣的寺院里。有的年近7旬的藏族老人,恭恭敬敬称孔繁森为自己的“父亲”。
孔繁森1994年11月29日殉职后,时任阿里地委宣扬部副部长柴腾虎与人合撰悼联:“六根清净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故里独恋雪域,置民族奇迹重如冈底斯山。”27年来,柴腾虎除有一年因事未能成行,年年到聊城祭奠孔繁森。墓园流连,一个声音从迢遥的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小城飘来: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由于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穿越时空,青年马克思的声音在高山景行者心中回荡。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