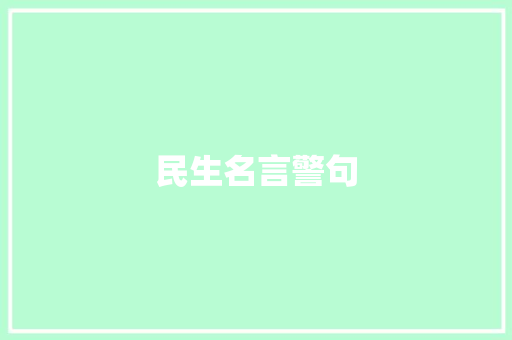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向来重视“民心”。“民心”向背每每被视为一个政权是否具备政治正当性的根本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深入民气的政治不雅观念,至今依然是我们提倡“民心政治”的主要思想资源。“民心”意味着公民对执政者的统治德行、能力以及效果的推戴与支持。然而,作为先秦学派代表人物的韩非子却反对“得民之心”,这在思想史上常被误解,以为法家反对“民心”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性,实际上这种解读偏离了韩非子的思想语境,应予以澄清。
韩非子反对得民心,根本缘故原由在于他立足于精英政治的视角,断定个体民众之于国家管理具有狭隘性。由此,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民心”(民众生理)潜在地蕴涵着与公共利益、长远利益的冲突特性,须要执政者有效地加以化解、管理。《韩非子·南面》讲:“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完备迎合民心之求,无益于鼓励奸邪行为。他认为,“民愚而不知乱”,百姓愚蠢而不睬解社会混乱的危害,以是明智的统治者不能完备按照百姓的想法去治国,相反,治国该当“反民心”:“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言下之意,很多精确的治国方法实在并非百姓内心喜好的,不能凡事都屈服百姓意愿。《韩非子·显学》也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韩非子认为“得民之心”的不雅观念是不睬解如何管理国家的天真想法,他追问:如果得民之心就可以,那按照百姓的想法去做就已足够,伊尹、管仲这样精彩的政治家基本就派不上用场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政治”之存在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以是,他进一步指出“民智不可用”,就像小孩子一样是愚蠢无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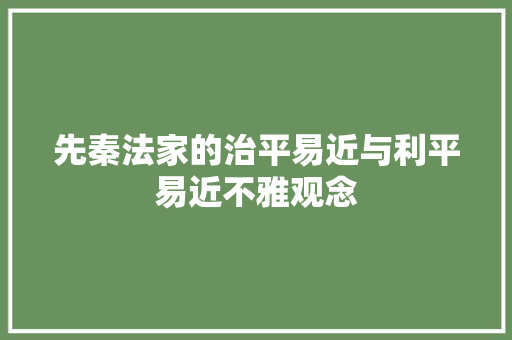
在此有三个问题须要特殊重视。第一,韩非子这种不雅观念是对孟子“民心论”的回应。《孟子·离娄上》明确说:“桀纣之失落天下也,失落其民也;失落其民者,失落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认为桀纣失落民心故失落天下,而欲得天下必得民心。得民心的方法在于知足民之所欲而杜绝民之所恶。这便是韩非子批评的“得民之心”的治国理念。在孟子看来,民之所欲便是“民心”,统治者必须知足民之所欲,才能得到百姓的推戴和支持,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以是这是政治正当性的根本。针对孟子的不雅观点,韩非子针锋相对地回应:民心所欲与所恶,难道就一定具有正当性吗?百姓总是想着自己的个人私利,鲜能关注公共利益与长远利益。在国家管理层面,韩非子就意识到百姓心里所思所欲,未必会符合政治领域特殊关注的长远利益与公共利益。韩非子对现实生活中百姓的繁芜生理具有深刻洞察:“大臣贪重,细民安乱。”(《韩非子·和氏》)百姓不喜好被管束,更不喜好严刑峻法:“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以是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以是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韩非子·奸劫弑臣》)国家管理涉及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每每非百姓之所喜。韩非子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反对凡事屈服百姓意愿的做法。很显然,孟子理解的“民心”是政治正当性意义上的百姓推戴与支持,而韩非子理解的“民心”却是履历生活中百姓的所欲所求存在偏私、狭隘乃至与公共利益相冲突。
第二,韩非子反对“得民之心”,因此民之大利为依归的。韩非子常以慈母对婴儿的办法来阐释其“民心论”。《韩非子·显学》说:“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孩子身上长了脓疮,此时须要慈母忍心用刀剖开以免病情进一步严重,就算孩子痛哭流涕也绝不心软。慈母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短长权衡,所做的事情虽然不为孩子所喜,但结果却为了孩子之大利。正是在此意义上,韩非子才明确讲“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可见,韩非子反对“得民之心”,并非意味着他不重视百姓利益,而是本着真正爱民的动机却做切实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韩非子·显学》说:“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敷用亦明矣。”韩非子从“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的结果中看到了凡事屈服百姓意愿对付公共事务来说是非常荒谬的。《韩非子·安危》也以扁鹊治病的事例来解释贤人治国要适当违逆民心:“砭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总之,韩非子反对“得民之心”,乃是意识到治国事关公共利益与长远利益,不能凡事屈服百姓意愿,乃至一定会制订违逆百姓意愿的制度。《韩非子·心度》阐述了“刑罚实为爱民”的不雅观点:“贤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以是恶民,爱之本也。”不从其欲,便是不屈服“民心”,但根本目的在于“利民”。统治者采取严刑峻法,并非仇恨百姓,而是防微杜渐式的“爱民”。终极,韩非子期待通过法家式的“爱民”“利民”来得到百姓的推戴与支持,从而实现政治正当性意义上的“得民心”。韩非子与孟子在“得民心”这一政治正当性的代价问题上,实际是殊途同归。
第三,韩非子秉持了“政治”具有专业属性的精英态度,凸显了“政治”的公共性。韩非子认为政治须要专门知识与技能。《韩非子·定法》说:“今治官者,智能也。”显然,年夜夫与工匠都具有专业属性,而政治领域的专业性则表示为“智能”,聪慧与能力。韩非子不相信百姓具备充分“智能”,纵然在沙场立过战功的勇士也被他打消在职业官位之外。他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宰相也好,将军也罢,都必须从基层一点点做起,这样才能表示充分的专业属性。韩非子明确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凸显出来。当他“政治地思考”民心问题时,他一定会认为百姓的知识与眼界不敷以应对具有公共性、全局性、专业性的政治事务。毋庸置疑,韩非子表示了明显的精英政治色彩,“贤人”是其空想中的政治精英。他期待君主与贤人合二为一,比如《韩非子·五蠹》期待历史重大关头涌现“新圣”。但是他也意识到在君主世袭制下君主为“中人”(《韩非子·难势》)的可能性,于是他又将空想中的“法术之士”如伊尹、太公、管仲等视为真正具备政治“智能”的精英:“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韩非子·南面》正是在此精英政治思维之下,精确的政治运作每每违逆履历生活中“民心”所欲所求。
韩非子的“民心论”,实为先秦法家“民心论”的理论总结。在政治正当性的问题上,《管子·牧民》明确强调“得民心”的主要性:“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养之。”《管子·正》说:“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显然,《管子·牧民》与孟子的思路是完备同等的,只不过《管子》利用百姓推戴和支持来实现君主统治目的的工具色彩更为浓厚:“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养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同时,《管子》也涉及大量国家管理不能屈服百姓意愿的不雅观点。《管子·法法》提出爱民实则用民的手段而非目的:“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用民,一定不会按照民之好恶为标准,而是按照法与国家的标准,欲民“舍所好而行所恶”。《商君书·开塞》也看到了民之好恶与国家管理之间的冲突:“现代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开塞》批评的“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的不雅观念,也是来自孟子,这是所谓“义”,而所谓“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之“不义”才是该篇作者所强调的。
《管子》《商君书》以及《韩非子》实际上都把稳到政治实践中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与百姓意愿之间的内在冲突,希望通过国家管理来实现国家富强并终极有利于百姓。法家跟其他先秦诸子一样,均预设了国家的终极目的不在君主个人利益而活着界人之利益:立君为民。法家认为,君主存在的意义在于凸显“公天下”的代价。《商君书·修权》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慎子·威德》亦谓:“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管子·正世》说:“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以是成功扬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韩非子·五蠹》则明确表达有巢氏、燧人氏之以是能够王天下的根本情由在于为百姓带去利益从而得到百姓推戴:“民悦之,使王天下。”国家或君主存在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害,这是一种“爱民”思路,也是一种终极通过政治效果来赢得“民心”的政治正当性不雅观念。显然,法家在立国原则及政治正当性问题层面,依然具有光鲜的代价诉求;但在现实管理层面,却更多强调了“民心”之繁芜性以及管理之必要性。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3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