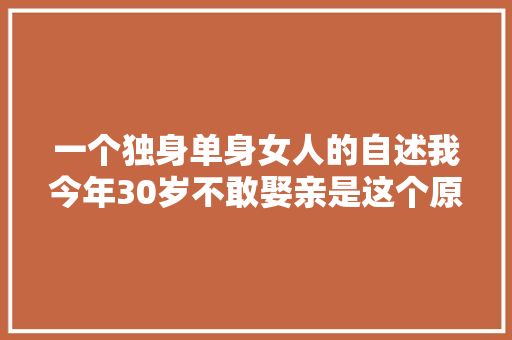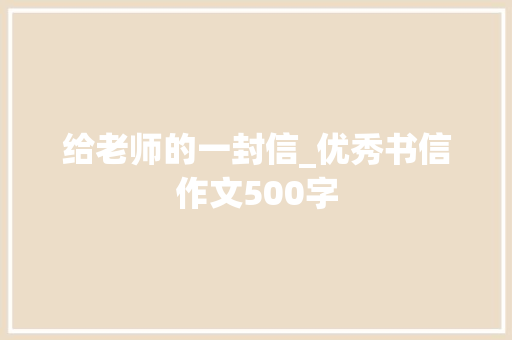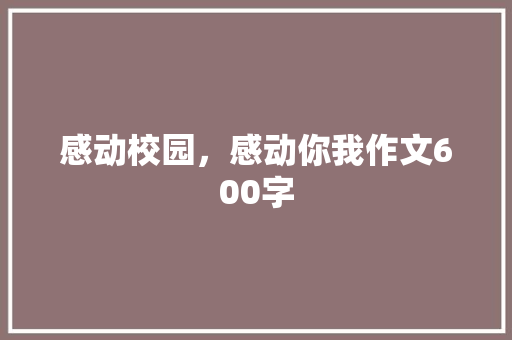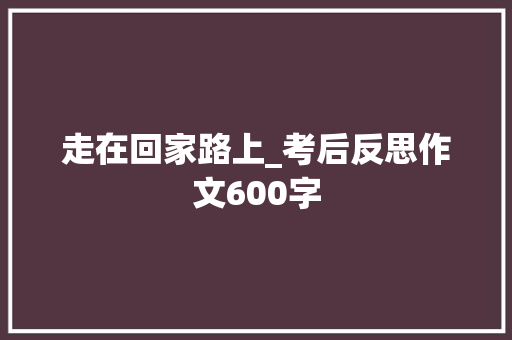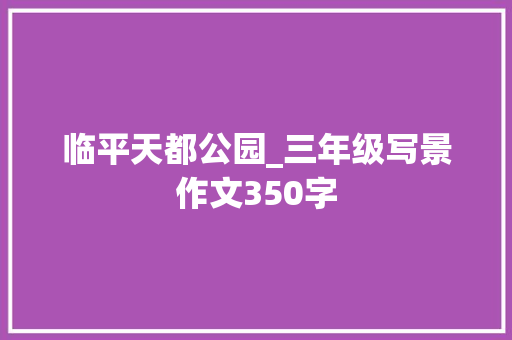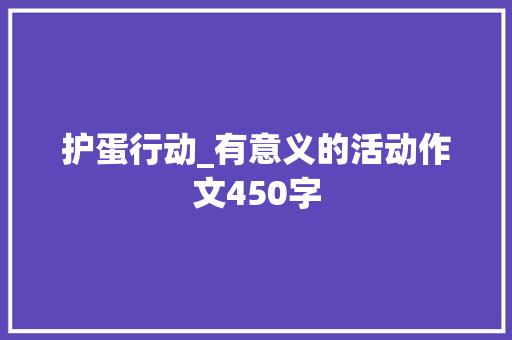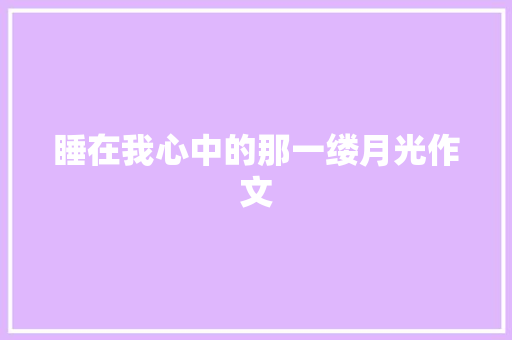2019年5月26日,患病住院期间的邹逸麟师长西席开始撰写回顾录,可惜由于身体缘故原由,写到同年6月2日戛然而止,下面是他末了告别天下的笔墨。这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回顾,对付理解1949年前后上海的市民生活,有一定的史料代价。
本文首发于《宁波文史》,经授权,澎湃新闻于邹师长西席九十冥诞之际转载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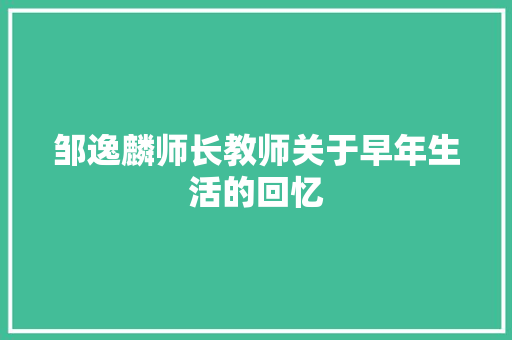
邹逸麟师长西席
我,邹逸麟2019年5月26日(周日)9:37A.M.开始写回顾录。地点在新华医院干部病房19号楼18层12床。
一、幼年回顾
我回顾起,我能记事大约在虚岁5岁时(1939年)。
我当时住在新闸路泰兴路附近的福康里(现改造成高档住宅区新福康里)。这是一种上海租界内中等水平的石库门屋子。底楼一层两间。中间是一间正厅,前有一天井,侧面是一间厢房,约有20余平方米。正厅后面是楼梯。上楼梯两楼同样是一正间和一厢房。再上去一楼梯通晒台,是全屋晒衣服的地方,没有卫生设备,各清闲家安设马桶。房屋的房东姓樊,安徽合肥人。樊先生长西席不大下楼,有时下来也是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马褂长袍,很少言谈。大约在政府部门干过差,有小官僚气,说话一句安徽北方话。
樊老太太是个很和气的人,整天笑呵呵的,大圆脸一脸福泽,最爱打麻将。整天在家打麻将,我妈不免敷衍,常常为麻伴。
樊家有四个小孩子,两男两女,老大女儿,老二男孩,老三女儿,老四儿子。最小的儿子大我约七八岁。我从小就叫他们大毛姊、小毛姊、大毛哥、小毛哥。我家住租他们家底楼一厢房间,大约20几平面,用家具一隔为二,前面部分是我父母的寝室,大间最高(窗外即天井)可以放一八仙桌和几把椅子,里面一间放一铜床,由保姆阿叶和我睡,当时我虚岁五岁。还有一家是在顶楼晒台旁一小亭子间,大约6-7平方,住了一家三小,一对年轻小夫妻,一小是和我同年的小女孩。男的彷佛没有正式事情,每天在家煮饭,不到底楼我们公用的厨房,就在屋内搞小炉子,女的不一定出去,我们其他两家都反面他们打呼唤,听说这个女子是舞女,大家也就不管了。唯这个小女孩是我最好的玩伴。由于樊家四个孩子与我年事相距太大,玩不起来,我不得不常常爬上楼梯在晒台上与她玩蚂蚁搬家。
1940年我大伯(生父)续弦,结婚时要男、女□□小傧相,我们便是一对。当时的照片很大,可惜“文革”时全给烧了,不知这小女孩(与我同年)还活着否?
我母亲讲原来我家住在闸北,八一三日本人轰炸,闸北全毁,百口逃来租界。先是数万人涌入租界,根本找不到住所,先租一家人阁楼,后来总算找到了福康里像样的住地,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生身父母原为长兄长嫂,三弟星如三十岁还无子息,又外婆做主,将我一胎生出即过继给三叔为子,这在我口述历史里讲得清楚了。由于是过继来的,从小即雇奶妈喂养,听说我奶妈是绍兴人(有照片)喂了八个月,她丈夫说因田里活很多,催着她回去,以是我只喝了八个月的人奶,往后一贯吃“生之可”的牛奶。奶妈走后,我母亲一人既要照顾家务,又要照顾我,顾不及用了一个保姆,名阿叶,浙江象隐士,从我小知事起就知道阿叶,她在我家一贯耽到1951年“三反五反”我家才丁宁她回家。阿叶天主教徒,本人没有文化,估计是家乡便是一个天主教徒□。没有听说有丈夫子女,有一弟弟(后说),每周日上午她都请假要去教堂做弥撒,我妈妈当然赞许。幼时生活都是她照顾我,记得我小时沐浴用一大白色搪瓷浴盆,我不爱沐浴,脱了衣服满地乱跑,她小脚赶不上我,就说:“弟弟、弟弟,小鸡落脱了。”当我低头察看时,她一把捉住我浸入水中。她还常说,我要洗到弟弟(指我)的孩子才退休。末了未能如愿。这个大白搪瓷浴盆,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才处理掉。往后一贯被我妈妈春节时浸糯米粉。
我小时的玩伴,三楼的小姑娘有时上去玩,樊家四个孩子与我岁数差距大,玩不在一起。有时还陵暴我。我小时候最爱吃城隍庙五喷鼻香豆,他们用肥皂刻了一个像五喷鼻香豆大小给我吃,辣得我眼泪直流,我妈妈就出头去讲了,你们不喜好他可以不理他,但不能陵暴他、作弄他,这样他们就不敢再陵暴我了。后来我们搬了家,与大毛姊还有来往的,记得我十岁时大毛姊还送了一合文具礼物。
我记得虚岁六岁上,开始一年级上学期(约1940年秋)读的是新闸路上允中女中附小(今改为爱国学校)。我记得开学第一天,父母为我买了一个小书包,像一个小皮箱,盖起来像一个小皮箱,开学第一天由阿叶陪我上学,记得教室坐满新同学,我叫阿叶坐在台上老师坐的位置上,一下子电铃响了,我知道老师来了,赶紧赶阿叶下台回家。学到年底,我们家搬到了戈登路(后改江宁路)727弄达德里46号,就将小学转到了文化小学。
二、达德里46号
四十年代新造的戈登路727弄(达德里)一群住宅,原是一块荒地,静安寺或普陀区之间,闸北过了海防路便是普陀区了,以是在当时是比较贫穷的地区。在这群新式里弄屋子建造之前,表面靠马路已经有一片住宅区,我们当是称为外弄堂,是两排十几家的旧式石库门屋子,标准与福康里差不多,每户都是底楼,一式厅、一厢房;二楼中有一亭子间,三楼即晒台。唯第一家姓沈的房在一层三间两厢房,“文革”期间没收后改为造反部,此是后话。里弄堂一共64户,房式因地块不同而格局不同,老式的是中间坐北朝南两排连体住宅,底楼前后两间分别约20平米、40平米,过来是一条楼梯通两楼,楼梯下刚好造了间小卫生间,再往里即厨房,刚新搬进去时还是用屯子式并排两座灶,一两楼梯间有一亭子间,即厨房的顶楼。两楼格式同,再上去即三楼已不分前后间了。一大间约20平米,前后房顶是斜的,窗户小,当时称假三层,这年地方上征房屋征税,即可便宜些。
我记得彷佛是1940年底搬进去的,当时我家一共四口,父母、阿叶和我。忽然住进这么多房间的独立一家,十分愉快。记得开始时这样布局的,底楼买了套红木家具,作客堂。二楼前室父母寝室,我那时还小,仅六岁,就和妈妈睡一被窝,二层前楼后间住着一个福康里搬来的大厨外,还堆了许多杂物。三楼一开始全无人住,堆了许多旧被子衣服等,用大布盖了起来,楼有时一个人上去看起来有些胆怯似的。
记得刚搬进新屋,曾出租过二间屋。一是亭子间记得租给一对老夫妇,听说是闸北逃难出来的无处居住,大约住了几个月就搬走的。二是外弄堂有家某姓大女儿结婚,新郎是外洋船员,一结婚就出国没有办新居,新婚一个月就在我家三楼暂作新居,白天在外家用饭,晚上来睡个觉。我家屋新,又在同一条弄堂里近便,以是我父母也就赞许了。记得大约也是住了一个月搬回去了。直至八十年代这家外弄堂人家还在,姓氏记不得了。
搬过江宁路后,我家生活在上海算上了一个档次,一是分开了马桶。这在当时城市居民生活中是件大事。新居正面窗用了钢窗,不受季风梅雨两时令影响,这也是上海居民生活条件提高的象征。
三、三个表姊一个姨妈
我们家一搬到达德里,周围穷亲戚都来依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内部关系一定结果。我父亲有兄弟七人姊妹三人。祖父母四十高下即撒手人寰,留下最大的儿子(静如)十八岁在吉林林业局谋生,老二早夭,老三(星如)即我养父只十三四岁,以下老四、老五页只差一岁。家中无人抚养,均托亲戚去做学徒,老六老七年不满十,不能做学徒,送入孤儿院就养。
三个姑妈,印象最深是大姑妈,因家里无人管理,大哥在外,家中事务即又大姑妈署理。大姑妈很早去世,嫁了男人张省三,我们称之为省三三姑丈,是个毫无能力的人,年青时抽过鸦片,说买过一次发财票,中了二千元险些发疯了。大姑妈去世后他一人也不知如何生活,凡节时常爱我家拜访。
大姑妈生有二女一男,一男不成料,北洋混战时不知参加什么军队着落不明,留下来两个女儿,悦琴、怡琴。悦琴岁数大些,小学文化,怡琴小些,也聪明。二人十余岁时即来住我家三楼。悦琴帮我妈做家务,而怡琴却由爸爸(她舅舅)培养读初中,初中毕业后,怡琴自己不想再念书了,由于统统学费生活费全靠三舅,实在不好意思,于我父母托邻居和她先容了一个男子,家庭中裕,本人工程师,该当不错的。但怡琴心思活动,彷佛对此男不敢兴趣,每次男友约她外出,她总带着我同去,即可以想知了。对方是合格正经的人家,哀求先订个婚,末了在南京路上康乐酒家,举行了订婚仪式,不料事隔不久,还是解约了。
女孩子解约耽在家里总不是办法,父亲就先容她到自己开的金国百货公司扮装品柜台当做事员,该当是很得当了,也有固定人为,不料怡琴不是一个循分的姑娘,当时在金国阛阓楼上有一座金国大戏院来演出话剧,演员都是有不三不四的年青人,个中有名的听说是原在喷鼻香港的女演员李绮年(1914—1950,原名李楚卿,广东人。为相识脱家庭穷苦,20岁那年,前往喷鼻香港大不雅观影片公司报考演员,一举得中,从此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当时拍摄的都是“粤语片”,个中有一部《生命线》,使李绮年得到了“爱国影星”的称号。)。周围簇拥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年青人,怡琴放工后不准时回家,常常在楼上与这批年青人混在一起,我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她训了一顿,她不高兴了,不告而别去宁波找她姊姊悦琴去了。悦琴已早几年经人先容嫁给了宁波老家一位男人,怡琴去了宁波,我们也不问了。后来听说在宁波经人先容嫁了一个老干部,后来转到甘肃河西走廊上一个新开拓矿业城市,大约有了局级太太的报酬,“文革”前六十年代还来过看望我们一次。怡琴姊大我十岁不到,从小陪我玩最多,常常一起去看电影,我记得最清楚,《浊世佳人》电影便是我和她一起安然电影院看的。当时我正在理发,她还到理发店里等我理好发一起去。
这是我父亲方面的表姊,我母亲有三个兄弟一姊姊,长兄、二兄早亡。长兄子有保,二兄子信根,都由我父亲推举在金国百货公司当职员,做到退休,三兄在镇海县城里当某药店总理,我们去过(抗降服利后)一次,他也来过上海一次住了几天,还专门去看了一场电影《太太万岁》。三兄有一子一女,女名阿应,原故意过房给我父母,但孩子不讨人喜好,未成。儿子张子玉读书不错,高中毕业考上上海医学院骨科,学习期间用度全由我父母支持。毕业后分在西岳医院骨科,结婚后每逢春节还常来拜年,后来也稀疏,我母亲患严重枢纽关头炎去找他,冷淡得很,彷佛不愿意回顾起从小沾恩于姑妈的事实。我们也不找他了。
我母亲方面长兄子有保下还有一个亲妹妹,叫宝胡,大约从小去纺织厂做童工,也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期间,后来经人先容嫁给了奉帮裁缝陈信章,是个很能干的裁缝。解放前专为有钱人订做西装,我们家大小男女洋装都是他做的,做功讲求。公私合营私人不能开业,并入1010军服厂,不能发挥浸染。
我母亲还有一个姊姊,我叫嬷嬷,年轻时嫁人做填房。男人去世后与前夫留下的女儿搞不好关系,就来沪投靠我母亲,也住在三楼。此人道格古怪,吃素不念经,话多。家里事,她样样要出主张,我父亲对她很讨厌,也不多与她说话,反正白天帮母亲做做针线,帮姨妈做做饭,她在宁波西门外有一套小房,一楼一底,前面靠马路,后马路一条小河,每天下午有抓鱼虾船走过买新鲜的,我去过一二天,太寂寞了。“三反五反”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她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回宁波,不久因尿毒症逝世,不过七十年,在我家里大约住了六七年。
四、二姑妈家
奇怪得很,我生平没有见过二姑妈,听说去世得早,大约不到四十岁,二姑丈倒时常见到。二姑丈名陈子展。书法家,为我父亲写个扇面,好不好也不懂,他个性与我们家人不合,听说他在银号业混,整天口中含一支雪茄,一套纺绸中装,一条腿有些瘸。说是从小落下的毛病,没听说做过正经买卖,生活还可以,生有二女一男,一个弟弟名小相,长得非常俊秀。与当今胡歌比较不输,还多两个酒窝,我大伯父再婚时当男傧相照片很俊秀,可惜“文革”间全烧了。
小相哥是我表哥,从小喜好带我出去嬉戏,玩的最多的陕西北路至南京西路一段,他中专读的是司帐,银行类。解放前在某国企谋职,解放后不相信这些留用职员,将他派去青海藏族地区一个银行里当事情职员。1980年退休回沪,对我说他们银行开门有西藏民进来存款,办好了,地上一堆大便,他们还要把它打消了。我年青非常崇拜他,负责他将来一定娶一个美女当妻了,不料生活坎坷,末了也在同样支内差错找了个又老又瘦的做终生伴侣,终极回上海还过得可以。1986年我母亲去世,伤悼会上他们家来过一次(我母亲是他的三舅母)往后就没有来往了。
五、文化小学
自1940年底家迁到达德利里后,1941年初一年级放学期只能转到戈登路达德里对马路的文化小学(后来改为静安区实验小学等名称),虽然只隔了一条马路,因我人小每天由阿叶陪同过马路,中午接回来用饭,下午再送过去。当时班级的主任是教语文的王西席,一个20多岁的女老师,她一样平常都是下午三时半教课结束,在学校办公室批改一二小时作业,大约5时旁边回家。我母亲就去学校拜托她放学后管一二小时,即让我在她办公室里做一二小时作业,不懂的可以辅导我。当她批改作业结束顺便带我过马路回家。我妈大约给她少量酬金,以表谢意。这是双方有我的事,大约1941年底大平洋战役发生,日军进驻租界,她家住在城里(南市区),晚了回去路上不屈安,就来我家向我妈妈辞了这事,当然这也无奈,往后也仍旧由阿叶接送。日陷时期每个小学都要学日语,还要唱东洋歌,学校请了一个有拉渣胡子的人唱日本歌,不知是真东洋人还是汉奸,反正小学生不好好学,胡绉,学校对这批小学生也无奈。
5月29日上午10时
六、金科中学
1946年夏,我文化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上什么中学呢?我们当时家的周围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普陀区新会路上晋元中学(市立),纪念谢晋元将军,一所即在胶州路余姚路交界的金科中学(天主教会学校)。那时我们弄堂里邻居多在金科中学。如后来我的舅兄戎熟年(长我两岁)也是进此学校的。
我在金科中学读书时,管理较严,英文西席大多来自徐汇中学的修士,语文、历史传授教化水平较高,专设孟子一课,本来规定进入高中开始学法文,后因解放当然不谈了,总之,学风还正,由于是男子中学无乱七八糟事,是解放落后修风气不如以前严格了。
我在金科中学念三年高中很不用功,除了语、外、史、地成绩还可以,数、理、化,常常不及格,要补考,老师瞥见我也头痛。我自己也实在不用功,上课看小说,不好好听。那时我读了许多小说:美国的德莱赛、俄国的契可夫、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哈代,还有基督山恩仇记……都是这期间看的,到大学才看《红楼梦》。以是1952年高考时,我根本不敢考理工科,考文史科。最后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还是生平幸运。
解放后政治缘故原由,非教徒不敢与教会同学多靠近,怕惹祸,末了我们只有三个要好的同学,徐士性、盛沛年和我。盛家有钱,住房宽,常常去他家补课,实际吃烤鸭,听音乐而已。至今80岁了,我和盛还有往来(口述历史有记。“口述历史”是指由邹逸麟口述,林丽成撰稿的《邹逸麟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
七、宝山与宝林
我父亲兄弟合伙约在1941年后,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与华侨饭店(当时称金门饭店)之间有一块空地建了金国阛阓,南面南京西路,北通黄河路,中间两侧建了十几家商店,中间有一条宽约三车道的走道,可让顾客步辇儿而过。我记得向南京路口两家商店,一家是恒源祥绒线店,一家是专卖北京甜食小品的翠文斋,自此进入两册有各色店铺,我们父辈即合伙开了两家金国百货公司。
那时我父亲买了一独轮包车,以便逐日出入之便。恰好有位朋友买了三轮车,将拉包车夫的宝山来帮我父亲拉车。宝山是南通人,身体高大,臂腿有力,每天早上约九时余,拉我父亲上金国百货公司,晚上拉回来。晚上便是我家客堂里两条长凳三块铺板,由我们供应铺盖睡觉。周日我父亲不上班,也就在家里帮阿叶做做厨房里的事,或外跑各差事。
我家原有一个小天井,种上一棵树,于是将树挖了,泥地铺上水泥,成了晚上包车的停车场。宝隐士诚笃规矩,做得很好,不料有一天拉我母亲去看病,不知如何一个急刹车,包车倒翻,将母亲翻在地上,我母亲的眼镜打碎一块小玻璃,插入眼皮下,闯了大祸,宝山吓坏了,说从此不敢再拉包车了,那时抗日战役胜利,上海又盛行三轮车了,我父亲就买了三轮车,宝山先容他弟弟宝林会踏三轮车,由他来承担,宝山也没有惩罚他,先容至我父亲的另一个企业光大毛织厂做杂务工。我家有了三轮车后,大门进不了,于是重新砌进门框,使三轮车可以进入大门天井,这大约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宝林人很诚笃规矩,一贯做到1951年,1952年“三反五反”,成本家哪再能坐三轮车?给我父亲转到太平洋织造厂做杂务工去了。宝林比宝山年轻,与我谈得拢,那时我已高中生,他教我如何踏三轮车,周日父亲不出去,我就在弄堂里骑三轮车玩,平时我上学早,七时半他先送我去学校,然后回家,再送我父亲上班。
八、金国百货公司
金国百货公司是我父辈兄弟合伙在四十年代在南京西路金国阛阓内开的,两爿日用百货店主要发卖男女亵服笠衫,棉毛衫、被单、毛巾、棉毛裤等日用织品。1945年抗降服利后,又加上扮装品柜台,以备社会须要。
金国百货,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该书的素材来自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及1949年版的《图录》下册,撷取了两册的内容精华编纂而成。
当时要在南京路上门面租金是很贵,发卖低档商品,根本付不起租金,而阛阓里店面租金低得多了,才能坚持下去,再则当时上海人逛南京路是一种体面、娱乐,普通收入的人不好意思上四大公司买低档商品,而阛阓里商品属于普通低档,这样就知足了他们逛南京路的虚荣心,又买得了生活实际须要的商品,以是阛阓里买卖还好,我记得阛阓里除我们两家百货店外,最多是皮鞋店,大约这种商品暂时不会坏的缘故。
两爿金国一共大约有十二三位职员,中午开两桌,由阿叶弟弟当厨,两桌饭是流水席,即到中午先开一桌三荤两素,一桌,谁有空先吃,第二桌时菜稍加补充,饭随吃,我也吃过几次,随父亲周末去玩,中午不外出吃,便是店后一饭厅吃,菜少油水,米籼米,勉强可吃饱。
晚上七时半打烊,有家属的店员,各自回家,有两个小徒弟,宁波出来的,便是店堂里搭铺睡觉,与我印象最深的是账房孙光递师长西席,高高瘦瘦的身子,每天在一个小账房里算账,有时放工了,也不回家,伏案写信,对我很好,常常把我抱坐在他膝盖上教我写羊毫字。上海解放前夕,忽然不辞而别,不久上海报上揭橥他当了某区商业局长,原来是潜伏在金国的地下党员。
抗降服利初,上海商业一度很繁荣,金国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也有一定名气,周日上午我常常跟父亲坐三轮车到公司来玩,他在办公室理账,我则在店堂里,或阛阓里瞎玩,中午我们父子常常到阛阓后门出去不远的“同春坊”四叔家里吃午饭。抗降服利后,四叔家人多,就从张家宅融和里租到国际饭店后门“同春坊”订了一套屋子,正房有六间,三楼还有几间佣人小屋,那时四婶家里开销很大,用了两个女佣,一个车夫,中午用饭人多,我和父亲即在几步之遥,就常常中午去蹭饭,后来父亲应酬多了,也不常去了。
还有值得一记的是,阛阓后门出口对马路有一爿小小“雪花咖啡馆”,我印象很深,是父子两人经营,店面很小。不过是一普通人家的客堂,放了四五个小方台,几把靠椅,只买牛奶咖啡和吐司面包,及小块白脱与果酱,东西都是外滩阛阓里从美国兵船上买来的,下午二三点钟,这里不少贩子店员来此吸烟、谈天,喝杯咖啡,吃块吐司,价钱低廉,顾客不少。我常常下午无去处,即在咖啡馆听听他们谈天,也颇故意思。
雪花咖啡馆。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该书的素材来自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及1949年版的《图录》下册,撷取了两册的内容精华编纂而成。
印象很深的是老板父亲,便是一个本日看了颇像老克勒,听说原来在外轮上当厨师,儿子二十多岁,跑外勤,穿上一套外滩中心阛阓买的美军制服,吹吹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