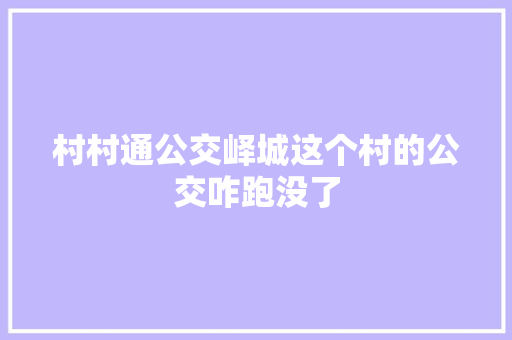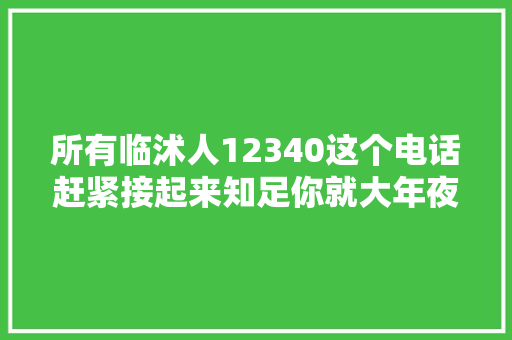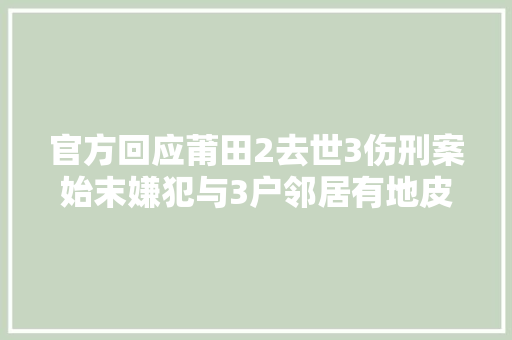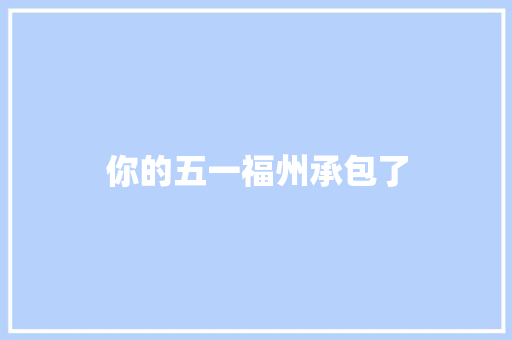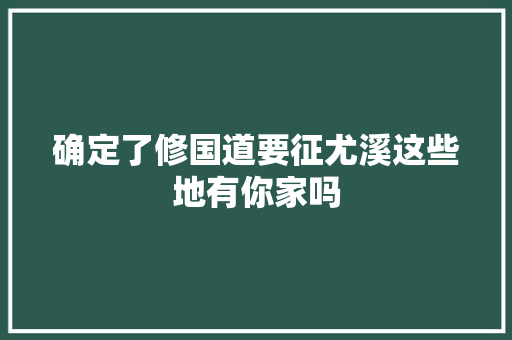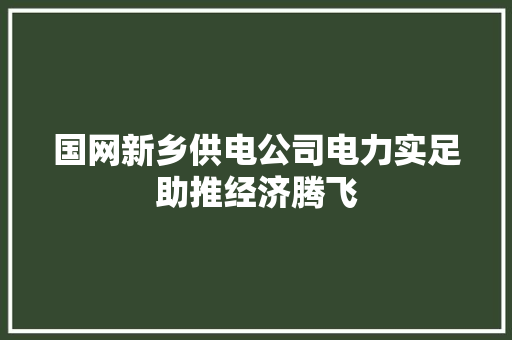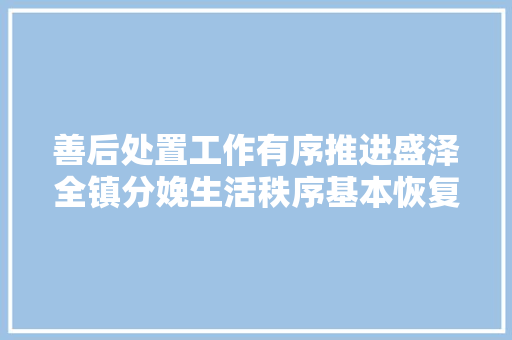有迹象显示,元代至正年间“南资都”作为定安故治时,中路驿道就已经成型,但铺设石板,当在明代中期。
难能名贵的是,目前还能看到将近一公里的中路石板驿道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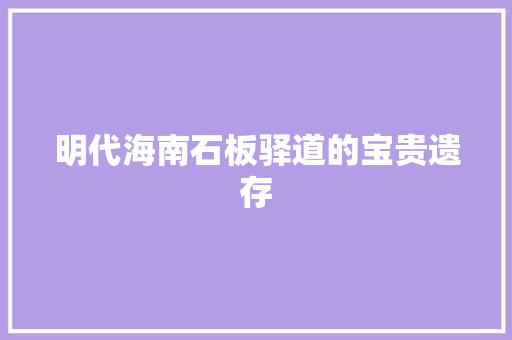
府城至定安驿道,是海南古驿道保存最完全的线路之一。该驿成型不晚于元至正,铺石不晚于明正德,走向及铺石记载清晰可考。现尚能看到石板遗迹的路段靠近一公里,石板较完全段约30米,非常宝贵。
但是,这个遗存至今不为人知,并未得到保护,随时可能消逝。
丁村落桥与谭押铺
海南的明代石板驿道,身份明确的极其稀少。
现存著名的两处古石板道,一在澄迈大丰(多峰)村落。但是,史载大丰墟明末清初曾离散,康熙间才重新形成,石板驿道铺于何时,史无明载。二是海口市遵谭镇的“五里官道”,修建于明万历,不过并非驿道,只是对科举的褒扬举动步伐。只有海口市北铺村落内,尚保存一段明末铺设的石板驿道。
海南古驿道有一条叫“中路”,自府城东南行,连接定安、会同两县,向来少人关注。在考据这条驿道时,笔者意外创造明代石板道的清晰遗存,与史料记载完备吻合。
正德《琼台志》对琼州府城至定安段驿道的铺舍,记载如下:
中路铺:谭抻(大来都)、挺村落(大挺都)、迈丰(郑都)、博门(东洋都)。以上属琼山。县门(附定安县。自府门铺至此一百四十五里)。
第一铺“谭抻”应是“谭押”之误,由于该志舆图作“谭押”,清代方志记作同音的“弹压”。
与铺名及所属的都对应的地名,当代均已消逝,但依然有迹可寻。
先看中路驿道如何出城。府城南行不远便是绕城而流的学前水(今美舍河),河上架有多道桥。民国《琼山县志》记载:
学前水,在郡城南。其源自西湖,流经丁村落桥,历洗马桥,绕旧学前,东至新桥、南桥……
丁村落桥,在县西南官道五里。水自西湖龙井来,经流洗马桥,达博冲河入海。
响水桥,在县南八里薛村落前。水自西湖流来,经此达博冲河入海。
府城以南多低洼湿地,只有南偏西方即丁村落方向,阵势较高,四季可通。以是美舍河诸桥中,唯有丁村落桥提到官道。方志多处说“西南官道”,正是由于驿道出城先西南行丁村落、薛村落,再南下之故。从里程看,中路第一铺谭押铺,大致在今薛村落附近。
乾桥与挺村落铺
第二铺,是挺村落铺。城南二十里有座乾桥,是方志提到官道的第二座桥,就在挺村落:
乾桥,在县南二十里挺村落官道(正德《琼台志》)。
干桥市,在大挺都,道光二十七年改为龙桥市(咸丰《琼山县志》)。
今版“干桥市”误用了简体字,乾桥乃“乾坤”之乾,乾坤与龙凤相通,故乾桥即龙桥。龙桥,超过的是南行驿道碰着的第三道小河。
龙桥镇街区,在海口以南约10公里,其北紧邻的挺丰村落,应系“挺村落”蜕变。市、镇之名皆源自桥。挺丰村落边有道小沟自西向东流,弯曲流向龙塘镇街以南入南渡江,古称“龙塘桥水”。驿道的“乾桥”就在其上,即今151县道公路桥位置。
沿路高下数里,再无他水,乾桥及挺村落铺位置得以确证。当年挺村落铺离府城直线间隔约二十里,由于略为绕远,谭押铺与挺村落铺的程距应各不小于十二里。
从迈丰铺至渡口
第三铺为迈丰铺,在郑都,位于今龙泉镇。
中路驿道穿行于南渡江下贱西岸,在山坡略高处取线,不受水潦影响。西岸数十里富饶河谷,是琼北主要古农耕文化带,沿线村落墟都图、古迹密集。
龙泉镇原名十字路,“十字路市,在县西南四十里,乾隆间设”。龙泉镇街以南,一反常态,溘然荒凉。沿县道4公里至今没有任何居民点,只有连片荒林,由于这里石多土薄,农耕难于发育。因此,驿道的迈丰铺,只能位于十字路村落墟区最南端。
迈丰铺南行,经由今日新坡镇以南的博门铺,抵达南渡江边的“博通渡”。
有关定安县城的渡口,请看光绪《定安县志》的记载:“博通渡,在(定安)城东北五里。明时琼、定各编渡夫一名。今废。”“北门渡,在(定安)城北,琼、澄往来要津。原设渡船、渡夫。”
《琼台志·定安舆图》描述博通渡在城东北,北来驿道自东门入城。定城原无北门,明中期甫开即闭,至康熙间,北门重开,离江边不过百余米。北上府城、西北去澄迈,皆由北门出,设北门渡,博通渡随废。
博通渡在定城东北五里的南渡江北岸,有“卜通村落”,今名“文丰村落”,渡口遗址无疑。
石板驿道历历可考
四铺位置的考据显示,当今连接府城至定城之间的X151县道,基本上与古驿道同线,是驿道的继续,老琼隐士称之为“定安老路”。
这段驿道穿越羊山地区,明代曾铺设过大段石板道,咸丰《琼山县志》采访册记载清晰:
西南官路离郡五里,俱系石地,迂曲波折,官吏艰于往来。明中叶间,庠生王用礼,大小偶都人,奉官督修。砌石二丈或丈余,宽狭不等,上自大来都,下至托都,凡六图,有五十里之遥,行者称便。
乡内都图,大致自北向南排列,最北是东潭都。龙塘都与大挺都,东西并列。修路的王用礼是更南的大小偶都人。
府城附近紧张通道,原来就铺设有石板道。但是,南路只铺了五里,即“县西南官道五里”之丁村落桥(属大来都),再远就没有铺了。王用礼奉命续修五十里,即铺石到城南五十五里之托都。
托都在哪里?民国《琼山县志》称“那抽市,在托都”,今美仁坡村落西三百米有那抽村落,其东,南渡江边有托村落,这一带便是托都。算里程,石板道应自丁村落桥铺到梁老桥。
梁老桥当代名称不改,所在的月塘溪显然是古遵化乡与其南面仁政乡的分界。桥北是遵化乡,桥南的梁陈都与梁老都等,均属仁政乡。大来都属府城南郊的丰好乡,其与遵化乡应以薛村落水为界。
石板驿道的铺设记载,又成为驿道走向的详细脚注,两者可以相互印证。
一段500年驿道
奇迹留存
离开龙泉镇街南行,县道很快就进入荒林,路面也显著变窄、被覆草率,根本不像县道。我以为走错了,当地人确证没错。
这段外面草野的县道,最靠近古驿原状,非常难得。更难得的是——明代石板驿道的一些片段,近一公里长度还清晰保存!
由于长期碾压,车辙带石块已严重破碎,但路中间部位,清晰的石块随处可见。沿路细察,这段路解放后似曾大略硬化,即在原来路面上铺一层较薄的水泥,但是碾压既久,水泥层破碎消逝,石块便重新袒露。
石板最无缺的路段,在X151县道与东环高速“十字路互通”匝道丁字路口以南,约1.46公里处。那里有条新修的小路向东,进入小居民点“十二房”。
这里,县道中心有长达30米、品相完全的石板道。石板为规整的长方形,横向铺设,排列紧密,工艺成熟。推测其原始宽度不少于一丈,符合县志记载荒僻路段的规格。大概更宽,但位于车辙带者已碾碎无存。这无疑都是王用礼督造的石板道,同时,反过来确证县道便是古驿道的扩宽版。
正德《琼台志》转载王佐在《琼台外记》的梁老桥诗,有“四顾山荒石路偏”一句,刻画了石板驿道之荒凉。王佐去世于正德前半期,因此,石板道应在此前铺设。
最迟正德前期铺设的石板道,距今已500年以上。在毫无保护的公路上人来车往,竟能留存至今,堪称奇迹!
这是多种缘故原由的巧合。一是由于历史上的中路驿道,交通不太繁忙。府城至定安之间有南渡江相连,货运多走水路,也避免了重载牛车长期碾压。
二是由于151县道不是干线,基本上是民国初年对驿道改造而成。由于至今尚未有桥直达定城,十字路以南交通冷僻,县道还是旧貌,弯弯曲曲,没有改造成钢筋水泥路面。
而最主要的是,龙泉镇以南的县道路段,受到高速公路无意中的保护。1990年代初,东环高速半幅通车。海南高速免费,而十字路与新坡均各有高速出口,这就将X151县道该段的车流大部吸引。否则,光是最近20年的大量车流,石板早就粉碎无存了……
诸多巧合,造成史有明载的明代石板驿道的罕见遗存。
以此为核心的这七八里县道,是海南“古驿游”的最佳路段。它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驿道的原始状态,串起沿线古村落古迹的来龙去脉,使之形成有机整体,不再伶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