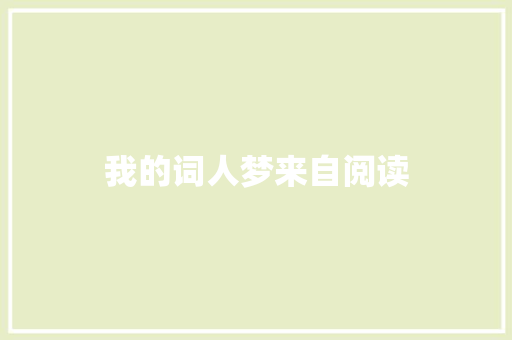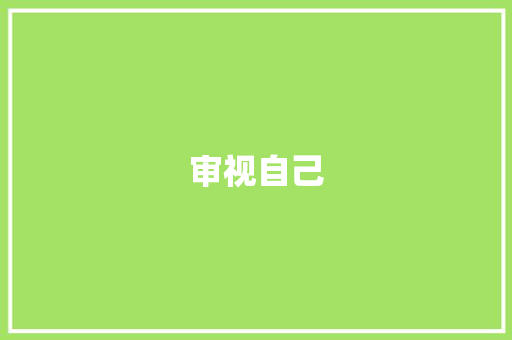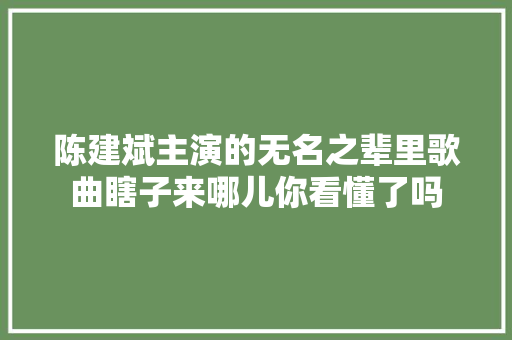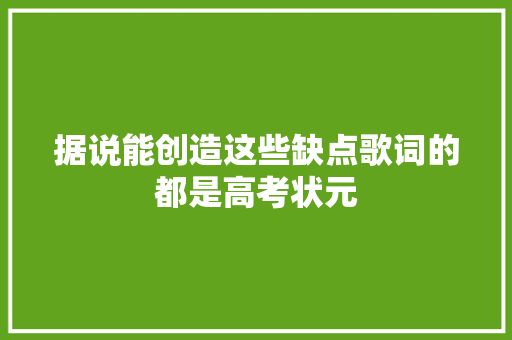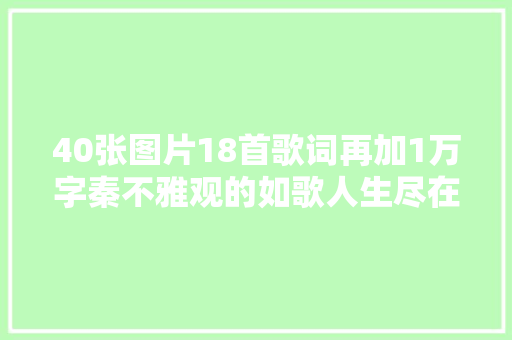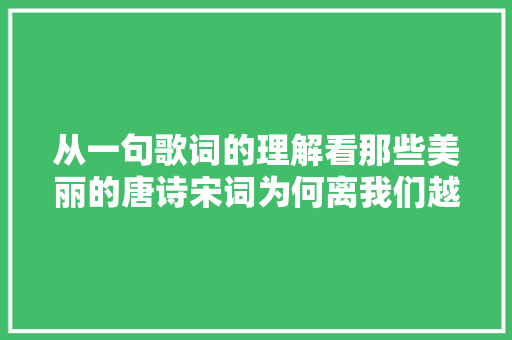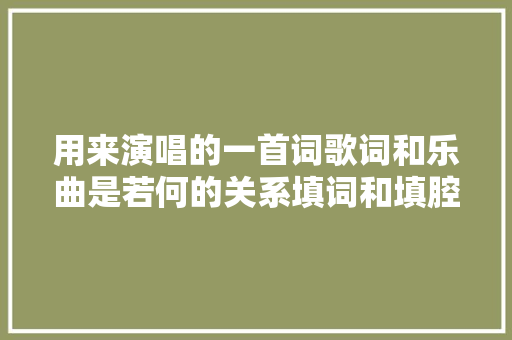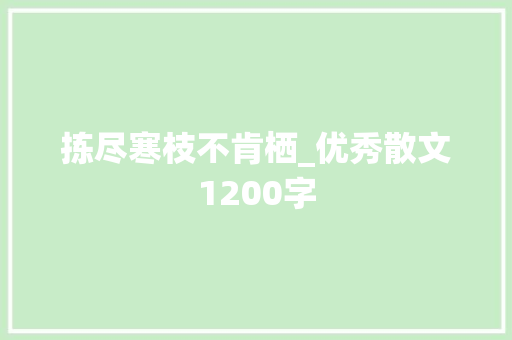正月为元月,十五为月圆之夜,故称正月十五为“元宵”。
早在汉明帝期间,已有元宵点灯敬佛的仪式,而后渐由宫廷发展到民间,由中原遍及南方各地。唐宋往后,元宵节更加盛况空前,十五日前后,或三五天,或长达十天,皇宫寺院,士民众庶,举国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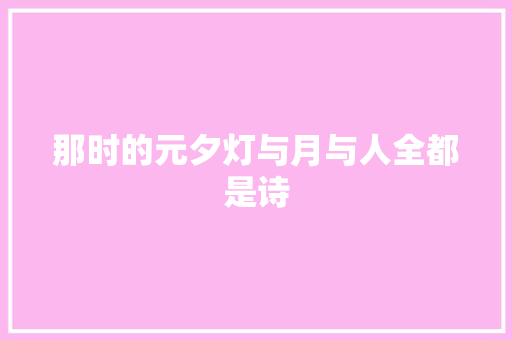
正月十五夜,都城驰禁,花灯如昼,人影参差,喷鼻香飘满路,钿车罗帕,更有暗尘随马……
那时的元夕,灯与月与人,全都是诗。
01
写的是元夕,还是爱情?
/ /
《青玉案·元夕》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喷鼻香满路,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顾,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
美是无法说出的。人在感想熏染到美时,却有表达的冲动。想要表达不可说的,只有用诗。大概这可以启迪我们什么是诗——诗,便是说出不可说的。这看似抵牾,看似玄奥,但犹如“道可道,非常道”,实在最靠近诗的实质。
以元夕为例。犹记儿时家乡的元宵节,十五夜进喷鼻香,灯笼队开路,锣鼓喧天,自村落广场逶迤而至戏台前。台上正中端坐着“玉皇大帝”,手捋一尺长的美髯,笑吟吟歆享万民同庆。最难忘的是,当烟花绽放,天下瞬间失落重,人像是漂浮在夜空。烟花照亮一张张脸,痴痴仰望,都不似平日的营营役役,彷佛那才是他们原来的自己。极短的一瞬又一瞬,静止如永恒,令人如梦而难醒。那种极美的体验,超出了任何措辞。
古时的元夕想必更美。很多诗人为此写了诗,想要说出并留下那种美,但很多诗仅止于铺陈罗列,结果平庸而失落败。就像一道美味佳肴,你只读到一些食材的名字,究竟无法尝到那道菜。
写元夕的诗词中,除却分外的个人偏好,公认最佳首推欧阳修和辛弃疾的词作。两首词我们都很熟习,先来读《青玉案·元夕》,看看大墨客辛弃疾是如何说出那无法说出的美。
若问这首词写的是元夕,还是一段浪漫的爱情?详细而言,元夕是爱情的背景,抑或爱情是元夕的组成?
实在答案已写在词的标题中,青玉案是词牌名,题目是“元夕”。词人要写的是元夕,而以浪漫美幻的爱情,陪衬出那个夜晚无法言说之美。
上片写元宵灯会的盛况,听说坐标是南宋都城临安,且让我们跟随墨客前往游赏一番。“东风夜放花千树”,点亮的灯笼,悬于枝头树杪,像东风吹开千树繁花。这个比喻实在不太恰当,“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树上的春雪和盛开的梨花在视觉和质感上很像,而花灯与花则无论在大小和质感上都有很大差异。大概词人正想以异质的类比,转而营造出瑶池的氛围吧。
“更吹落,星如雨”,有说是灯焰飘落的火星儿,有说是烟花,我们不妨认为是烟花。烟花绽放之后,焰火纷纭坠落,更像流星。东风为花灯和焰火注入了艺术觉得。有了风,万物才会灵动。东风款款,灯笼摇荡,焰火飘落如星。
再看街市上的景象。“宝马雕车喷鼻香满路,凤箫声动”,车马喧填,鼓乐如沸,极为繁华绮丽。又有“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灯月交辉,舞鱼舞龙的社火百戏,终夜不息。
以上铺排令人目不暇接,若只写这些,也不过便是热闹,而且通过笔墨,我们也未必能切身感想熏染到。再来看词的下片,由景至人,有了那人,风景才有灵魂。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蛾儿、雪柳、黄金缕,都是古代妇女元夜时戴在头上的装饰,她们笑语盈盈,暗香来去。元夕盛况通宵达旦,平日深居简出的女子,此时结伴艳服嬉戏,衣喷鼻香灯影恍若瑶池,哪能不发生点儿爱情?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顾,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即是她,即是那人。谁是那人?说法有三:女子,词人自己,失落去的汴京。梁启超在《艺蘅馆词选》丙卷中说,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但若因此指称那人便是词人自己或汴京,实在是疑神疑鬼不敷为据。
辛弃疾终生寄望收复神州,但如果在热闹的元宵节,非要如此肉麻地将汴京比作爱情,难免不免太煞风景。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乃词人在政治空想失落落之后,渴望遇见一位俏丽的女性,作为身心归隐的桃花源。这难道不是古代条记小说常见的主题吗?
那人正是这样脱俗的女子,她不在万头攒动灯火辉煌之处。众里寻她千百度,就在你失落望怠倦时,蓦然回顾,她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句的确非大词人不能道,大词人不是指名气大,而是才华和灵魂的深度。生命中这样的体验很神秘,词人懂得不必道破,就在奇迹发生的一瞬,韶光定格。那人是谁,后来若何,都不主要,此一瞬已经足够。
通读一遍,末了,我们也蓦然回顾,创造这首词貌似写爱情,实则与爱情无关,词人所写的应是自己“一个人的元夕”。
李嵩(南宋)《不雅观灯图轴》
02
去年今日元夜时
/ /
《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薄暮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 /
此词曾误入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的《断肠集》,后经明代学者澄清,乃出自《欧阳文忠公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味其风格,当为欧阳修词无疑,读者可自行求证。
这首广为传诵的词,简约朴实,清新耐读,一读即能成诵。词中所写,可以是古代任何一个元夜,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以是大家爱读,大家读了皆如得我心者。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一个主要的诗学不雅观点,即“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写诗(包括写词)靠的不是学问,虽然博学可能会给你一些底气,但诗写得好不好靠的是天赋,即天生的感想熏染和洞察力,这是很难外求的。欧阳修非不博学也,但我们读他的词,看不到炫耀学问或掉书袋,他写词亲切朴素浑然天成。一个真正的墨客,他的学问是流淌在血液中的。
好诗的深刻,也无关思想与晦涩,乃表示于能将万物间隐秘的关系,以貌似大略的视像揭示出来。若论深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表面的东西最深刻。
欧阳修这首词大略但深刻,就在于他揭示出了表面的事物背后隐秘的关系,而且是用近乎民歌的措辞唱了出来。谁读了都懂,但墨客不是要你懂他写了什么,是要你去体验个中的人生。
去年的元夜,犹今年的元夜;今年的元夜,却迥异于去年的元夜。月依旧,灯依旧,但人变了,而人变了,统统就都变了。元夜不但是个背景,这个夜晚的时空,以及构成它的统统事物,都是故事的参与者,都已经与影象融为一体。当墨客重返现场,去年的情景仍在,但去年那个人不在了,墨客只好以诗来歌唱失落落的幸福。
这首词很随意马虎让人想起唐代墨客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都是去年今日,都是一个人消逝了,吊唁的都是短暂的爱情。不同在于,《生查子》词中还有回顾,而崔护诗中却还没来得及发生。
佚名(明)《上元灯彩图》
03
元宵是一群人的狂欢
/ /
《迎新春(大石调)》
柳永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
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
遍九陌、罗绮喷鼻香风微度。
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
渐天如水,素月当午。喷鼻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
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每每奇遇。
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
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 /
以诗意论,上面欧、辛二人的词是诗,柳永此词具有诗的形式,但内容是散文的。柳永的很多词,如果抛开音乐演唱,单就文本而言,实在都是散文或眇小说。古典诗歌中有很多诗并无诗意,比如某些交际应酬之作,不过是按照平仄韵律写出来的乏味散文。我们读古诗须要炼出这样的目光,即要能辨认出诗的真伪。
当然,柳永的创作有所不同。毕竟他写的是歌词,并且自己大量编曲,白描、铺叙以及俚语鄙谚,这类散文或小说化的笔法,都是他对“词”这种歌唱艺术的创新,应首先把他当作音乐人。
对付一位音乐人,曲调要比可更换的歌词主要得多。“迎新春”词调,即为柳永所创制,据称因所押之韵极险,故后人无复用者,遂成孤调。遗憾的是,其乐调早已失落传,我们只能读读歌词,单就歌词很难对其艺术加以评判。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且将此词当作一篇写北宋都城汴京元宵节的散文来读。词人以白描笔法,为我们铺叙出了当时的热闹景象。前几句交代时序变迁,冬去春来,景象晴暖,又是元宵佳节。“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喷鼻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只需将这些词句,逐个还原为画面,大致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
下片写到游人的活动,在本日看来前卫有趣。已至午夜,灯也看够了,男男女女各自寻欢。“喷鼻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绝缨、掷果都是典故,意指男女相悦示好。“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每每奇遇”,则更有风骚艳遇,幽期密约。
从华灯盛景与世态人情,作者看到的是“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如他所说,元宵夜随分良聚,并没什么好坏对错,他自己也但愿沉醉个中。然而,从这句话及整首词疏淡的语调来看,很不幸他是他并不想成为的独醒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正:李世辉。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