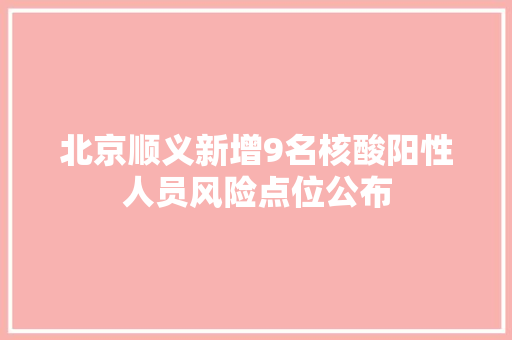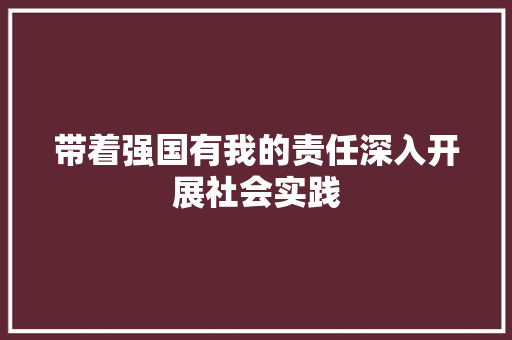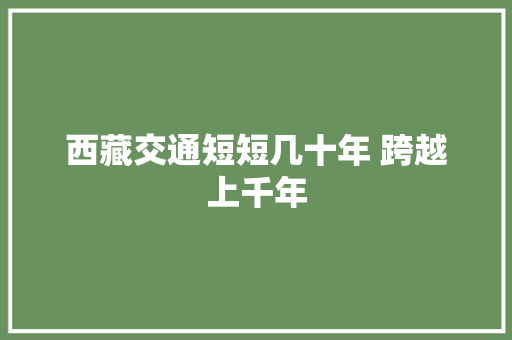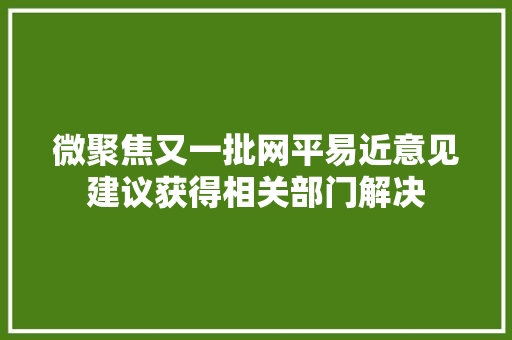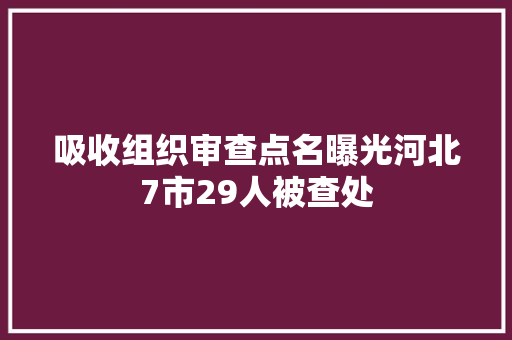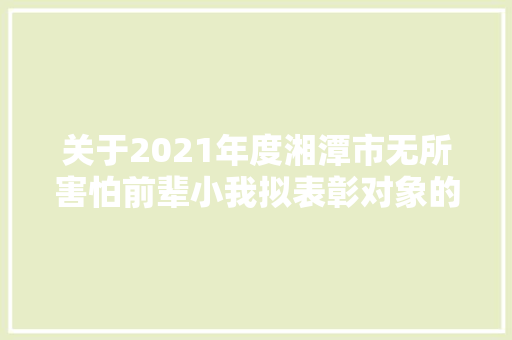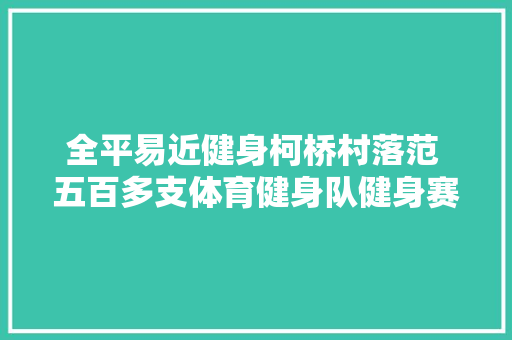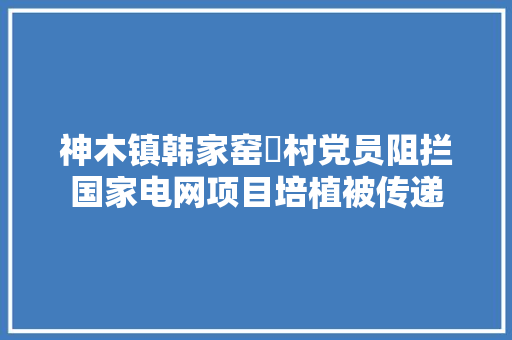格拉丹东雪山。 许明远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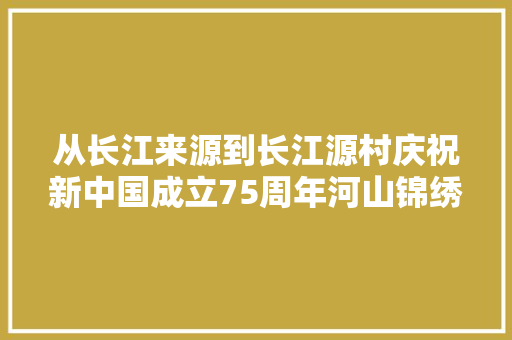
从青海省格尔木市沿青藏公路一起驱车向南,我一贯默不作声地盯视着昆仑山莽莽苍苍的山影,那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的积雪寒光逼人。车上正放着一曲《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这荡气回肠的歌声,先声夺人,一下就把我带进了长江源头。
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是长江源头之一。那无穷的源泉、纯洁的清流和回荡在天外的涛声,最初便是在雪山冰川中孕育和出身,这便是长江正源沱沱河。沱沱河流经的第一个州里,便是被誉为“长江源头第一镇”的唐古拉山镇。
我要探访的长江源村落,是唐古拉山镇的一个生态移民村落,距唐古拉山镇还有400多公里。
穿过一座座藏式风格的牌楼,可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村落里转了几圈,几经打听,我才找到更尕南杰老人的家。他是村落里的老支书,也是第一个带头从沱沱河边搬到这里来的牧人。
若要打听长江源村落的来龙去脉,没有谁比他更熟习。一看老人那走路的姿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在马背上游牧了大半辈子的牧人。
一说到游牧生活,他老人家的话就像沱沱河一样滔滔不绝……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游牧更自由清闲的生活?看着老人那闪烁发亮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又走神了,仿佛又纵身跃上了马背,叭叭叭地甩响了牧鞭,吆喝着奔向草原的牛羊。更尕南杰一家祖祖辈辈都在那雄鹰飞不过的唐古拉山和沱沱河边游牧,哪里有水源,哪里便有草甸,哪里便有牧民搭起的帐篷和他们放牧的牛羊。牧人们时常在草甸上围成一圈,一边热乎乎地喝着铜壶里的酥油茶,一边放开喉咙对着格拉丹东雪山歌唱。他们最爱唱的是《拉姆梅朵》,这首古老的藏歌我是听不懂的,但我能觉得到歌声里洋溢的欢快,那是从草原上成长出来的。
谁又知道,这些欢快背后有多少艰辛和苦楚?在海拔那样高的地方,别看他们守着一条沱沱河,但长江源头每年冰冻期长达9个月。那时候,更尕南杰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水开始。天一亮,他就会背着一只水桶去冰川下驮水。那是世上最难走的路,在冰川退缩后,留下了一堆堆尖利的乱石和野兽白森森的骨骸。哪怕穿着牦牛皮靴子,也感到脚心一阵阵扎心的痛。当他当心翼翼地靠近冰舌时,从风中模糊传来水声,那声音仿佛是从某个空洞里发出的,很小、很深,一样平常人听不见,但他对水声格外敏感,听得清清楚楚,那是冰川底下融化的冰水。这冰川乍一看彷佛没什么变革,但冰川底下是一个个早已被掏空了的窟窿,只要用脚轻轻一踩,就会有大块的冰川坍塌。每次打水,更尕南杰都小心翼翼,当他驮着水回来时要更加小心,恐怕洒出去一滴水。这每一滴水都是命根子啊!
一个对水特殊敏感的牧人,一度见证了长江源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急。唐古拉山镇是高海拔州里,那稀稀拉拉的草紧贴着土地成长,每年6月初才逐步泛出一丝绿意,一到8月下旬草甸就开始枯黄。若是遭遇沙尘暴或狂风雪,薄薄的一层草甸就被风沙和大雪挡住了。牛羊没有草吃就会活活饿去世,这样的灾害在唐古拉山、沱沱河边轮番上演,愈演愈烈。唐古拉山的牧民,一年到头骑在马背上,住在帐篷里,每天起得比太阳还早,每天睡得比玉轮还晚,他们就这样起早贪黑地放牛放羊,从20世纪放到21世纪,每年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为了生存,更尕南杰和他的牧民兄弟只能不断增加牛羊的数量,吃光一片草甸就换一片草甸,牛羊越放越远,游牧的路越来越长,一贯放到了长江源头的冰舌下,那草越来越稀了,牛羊也越来越瘦了,这草场越来越养不活这么多牛羊和牧民了。
一个在沱沱河边游牧了大半辈子的牧人,越来越明白,牧民是靠牛羊养活的,牛羊是靠草原养活的,草原是靠河流养活的,河流是靠雪山冰川养活的,这雪山、冰川、草原、牧人、牛羊,还有那熊啊、狼啊、藏羚羊啊等各种野生动物,组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然生态系统。而草场还是那么大,人口和牛羊还在不断增长,怎么办?
二
当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迁居到一个更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去,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在生态与生存的博弈中,唐古拉山镇作为“长江源头第一镇”,一贯承担着守护长江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樊篱的职责。2004年起,唐古拉山镇100多户、400多名牧民相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从沱沱河边自发迁居至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方案培植的新村落。这个新村落便是本日的生态移民村落——长江源村落。
迁居,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长江源,逐步减少长江源生态核心区的人类活动,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地牧民的命运。这也是生态与生存的决议中,别无选择的选择。
按说,从这高寒缺氧、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迁居到一个海拔更低、更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那是天算夜的好事啊。对付这些一年四季到处转场的牧民来说,搬家实在不算什么,他们难以割舍的不是装在马褡子里的帐篷之家,而是草原和他们的牛羊。更尕南杰从小就随着父亲在长江源头游牧,他一贯在心里记住父亲病笃之际的叮嘱:“不管碰着什么情形,你都不要丢弃这座雪山、这片草场啊!”
他从来没有忘却父亲的临终叮嘱,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放下牧鞭,离开祖祖辈辈游牧的草场和牛羊。可是,若不走出这座雪山、这片草场,这里的牧民兄弟和牛羊就再也没有活路了。
在更尕南杰的奔忙游说下,牧民们几经犹疑后,终极决定随着更尕南杰一起搬。更尕南杰还记得,第一批牧民迁居时是冬天,搬家的车一贯沿着沱沱河边走,眼看就要告别沱沱河了,骤然响起一片哭声,女人们都哭成了泪人,连那些像野牦牛一样壮实的男人也一个个哭得眼睛通红。当汽车翻越昆仑山时,大伙儿还眼巴巴地回望着唐古拉山的方向。从此,他们游牧的草场就变成了迢遥的故乡。
从马背上的牧人到长江源村落村落民,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这是更尕南杰和唐古拉山牧民的一次集体转型。但猛地一想,他们从马背上、帐篷里搬到这里来,又能干什么呢?
早在移民迁居之前,当地政府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若要这些移民在长江源村落扎下根,他们无疑须要换一种活法、闯出一条活路。为此,当地政府部门在村落里开办了一系列技能培训班,从汽车驾驶到摩托车修理,从玛尼石雕刻到藏毯编织,还有畜生养肥、牛羊肉贸易和厨艺、茶艺培训班。这些实实在在的培训,都能实实在在派上用场。
闹布才仁是一个头脑活络的牧民,刚搬过来时他也有过一段韶光的茫然。没事时,他就到外边去转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出路。这一找还真被他找到了,那便是开卡车,跑运输。一旦认准了这条路,他随即参加了汽车驾驶培训班,又在村落里第一个拿到了货车驾照。有了这个黑底金字的硬本本,他的腰杆一下硬了,便拿出多年积蓄,加上一笔生态移民自主创业的优惠贷款,买下一辆东风牌翻斗车。就这样,一个马背上的牧民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握着方向盘的货车司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型。他跑了10年运输,既挣到了票子,还见了世面,又捕捉到一个绝好的商机。这车轱辘转来转去,在闹布才仁脑筋里转出一个新动机,他利用开货车、跑运输的便利,每年回唐古拉山收购牛羊。这一转,便是一个牧民的第二次转型,从货车司机变成了商贸老板。闹布才仁还在村落里注册了一家格尔木岗尖蕃巴商贸公司。“岗尖蕃巴”,在藏语中便是高原雪山的意思。
我来长江源村落探访时,闹布才仁身边围着一圈来采购生鲜牛羊肉的顾客,他指着自己的招牌对顾客说:“看看,岗尖蕃巴,高原雪山,我这牛羊肉都是在高原雪山上终年夜的,喝的是雪山水,吃的是中草药,个顶个的膘肥体壮,那味道好得很呢!”
闹布才仁,堪称是唐古拉山牧民成功转型的一个缩影。更尕南杰老支书笑呵呵地说:“这样的人在村落里还多着呢。”
走进村落街东南边的一座院落,这里开着一家岗布巴民族手工艺品专业互助社。那个穿着一身靓丽藏服的女子,便是这家互助社的创办人三木吉。她是村落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也是长江源村落第一位回村落创业的大学生。当牧民们从唐古拉山搬到格尔木市郊,三木吉不乏担心。她记起自己小时候,家家户户穿的藏服、藏靴,用的氆氇、唐卡、门帘都是民间手工制作的,每一件都是有着浓郁藏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三木吉思来想去,开起了一家专业互助社,带领村落里的妇女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制作,这还真是一个两全其美、一石二鸟的好主张。看看,这互助社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手工艺品,那日月星辰的图案,源自藏族对天宇的崇奉,那鲜活的格桑花、圣洁的雪莲花,又源自藏族的自然崇奉。这些手工艺品既是都雅之物,也是圣洁之物,每一件都带着工匠的体温。这些年,三木吉穿着一身藏服奔波于各大城市推广民族手工艺品,或带着互助社的产品亮相于省内外的大型展会。她们制作的藏式氆氇毯一贯供不应求,纯羊绒围巾已远销尼泊尔。现在,三木吉还打算从村落里接管更多妇女加入互助社,她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到传统民族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中来,这也是她更高、更长远的追求。
从闹布才仁的转型到三木吉的追求可以看到,这些生态移民已把家当从村落里延伸到城市,又把城市的经营理念带回村落里,把一条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活了。走在一条条村落街上,两边便是一排排临街门面和琳琅满目的招牌,藏餐馆、藏茶馆、藏驿站、藏族饰品店、唐古拉山土特产店、玛尼石雕刻车间、藏族民俗展示演绎厅、长江源藏民族风情园……每一块招牌背后都有一个转型创业的故事,这些易地迁居的唐古拉山牧民不但是换了一个生活的地方,而是每个人都换了一种活法。
当我穿行在这生态移民新村落,在蓝天映衬下,觉得统统都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清新、干净、透亮,那洁白与赭红相间的房屋,一如白皑皑的雪山与赭赤色的高原。这是一个日月牙异的村落寨,却又保存了雪域高原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也是原生态啊。在迎面而来的阳光里,一个个穿着藏服的身影,一张张洋溢着欣悦的笑脸,安适,宁静,吉祥,怡然自乐,扎西德勒!
三
回顾当年,这些牧民为了保护长江源头的自然生态,搬离了祖祖辈辈游牧的家园,过上了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但他们梦见最多的依然是雪山、冰川、河流、草原和牛羊。他们虽说放下了牧鞭,却依然是草原的主人。作为生态移民,他们有些人从草原的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员,那是一个个像草一样从草原上成长出来的生态守护者。
闹布桑周是长江源村落最早的一批生态管护员。迁居那年,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一股子骑在马背上的慓悍劲儿,让他觉得特殊神气。只是,那贫瘠而薄弱的草甸再也经不起马蹄的践踏和牛羊的啃食了,这也是他最担心的。当更尕南杰等村落干部几次上门来做迁居动员时,只管闹布桑周舍不得离开家乡,但他也知道,这样下去草场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难以养活一家人。那就搬吧!他终于点头时,觉得自己的脖颈都是僵硬的。迁居那天,他从沱沱河滩上捡来两块巴掌大的石头,一贯放在家里的窗台上。每当阳光透过宽敞通亮的窗户照进来,最先照亮的便是这两块石头,它们在阳光下像沱沱河一样闪烁着波光。闹布桑周时常看着石头兀自入迷,一走神就走到了沱沱河边。当长江源村落招募生态管护员时,他险些连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这还真是不用去想。这些年他开着越野车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但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喜好的还是沱沱河边的故乡,那是他生命的源头,他永久都是长江源头的孩子。
对付这些生态移民,守护长江源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没的说。他们从未忘怀自己的母亲河,他们也笃信母亲河不会忘却他们,一贯惦记着他们。守护母亲河,对付他们不但是一份任务,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怀。
自从当上了生态管护员,闹布桑周每月都要开着自家的越野车,翻越昆仑山,重返唐古拉,走向那熟习的雪山、冰川、河流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一个起先的牧人,还是那样慓悍,他头戴牛仔帽,身穿迷彩服,足蹬一双硕大的马靴,胸前挂着望远镜和摄影机,身后还背着一把水壶、一袋风干肉和一袋糌粑。每一次例行巡护,他都要把自己管护的任务区走上一圈,这一圈要走多久则要看景象和路况,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一起上,他要仔细不雅观察草场、水情和雪线的变革,连一枝一叶一朵野花也不能轻易放过。尤其是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植物,今年在哪片草场上的长势比较繁茂,植株有多高,花冠直径有多大,都要拍摄和记录下来,并做上标记,到了来年的同一时节再来不雅观察和比较,看这栽种物是长得更繁茂了,还是退化了?除了这些常规监测,生态管护员还要时时关注生态环境的非常情形,如果河流湖泊遭到污染,有人盗挖野生植物或盗猎野生动物,或是有受伤被困的野生动物急需救助,生态管护员都要第一韶光向镇上报告。由于草原深处没有手机通讯网络,生态管护员只能通过对讲机通报信息,一个生态管护员有时候要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坡上才能将信息通报给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然后一个接一个依次通报出去,这是保护长江源生态的一场接力赛……
长江源村落现有200多名生态管护员,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个,全面覆盖了长江源头500多万亩禁牧区。更尕南杰老支书也曾是村落里最早一批生态管护员,如今他年近古稀,已把生态管护的接力棒交给了子女。而从长江源头到长江源村落,依然是老支书心里最深的顾虑。他给我算了两笔账,一笔是村落民的收入账,从迁居之前每年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到如今人均年收入已超过3万元,20年翻了15倍。还有一笔账,最近20年,长江源头的牧人和牛羊少了,草越来越多了,沱沱河水越来越清了。近期监测统计数据显示,长江源区的各种草地产草量提高了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
这两笔账的背后,是人类在生存与生态的博弈中探索出的一种可推广模式,这种社区和村落民自治共管的生态环境管理模式,从尊重牧民或村落民主体地位出发,引发了他们保护自然生态的主动性。过去是“国家给钱让我保护”,现在是“自觉自发地保护”,过去是家家盼温饱、大家谋生计,现在是家家管生态、大家争当环保卫士,这才是一个生态移民村落最根本的转型。
当我跟这位豁达而快活的老人作别时,天色已晚,一轮巨大的夕阳正在昆仑山降临,而在山的那一边,一轮圆月也正在冉冉升起。老人一边朝我挥手作别,一边迈着唐古拉牧人惯有的步伐,一步,一步,不疾不徐,仿佛依然走在沱沱河边的草原上。那个日月交映下的身影,被光阴拉得悠远而漫长,从风声中传来的歌声,又是那首《拉姆梅朵》。这首藏歌我竟然逐渐听懂了,那每一个音符都洋溢着“众生眼中之美,有情心中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