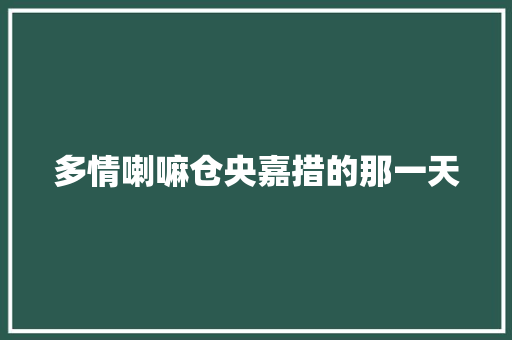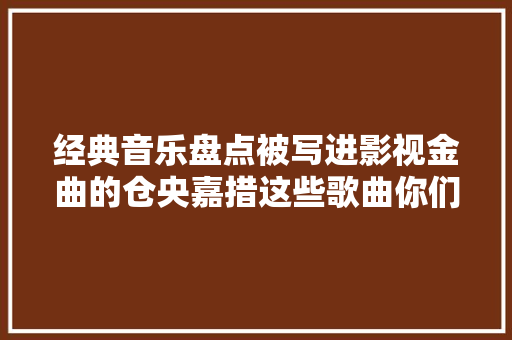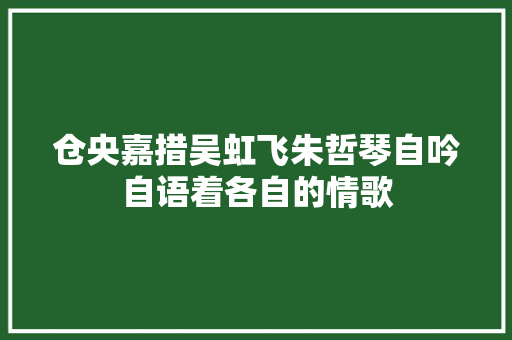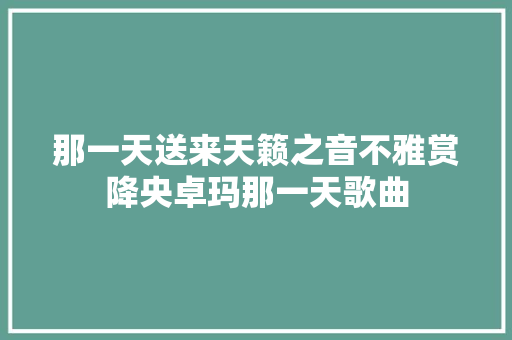仓央嘉措的诗歌,在藏族及蒙族中广为传唱,流传了三百余年耐久不衰,成了名副实在的“雪域诗王”、“一代诗圣”①;现今,由于信息的便利与快捷,仓央嘉措的诗歌现已传遍全天下,称其为“西藏诗圣”,该当不是言过实在。
在这些汇编的诗歌中,据一位我国著名的蒙古措辞学者的说法,刘家驹、苏朗甲措、周良沛、于道泉等人所翻译的较为准确②,即比较尊重原著(即不论境界高低、文词利害,只论是否符合原著作品的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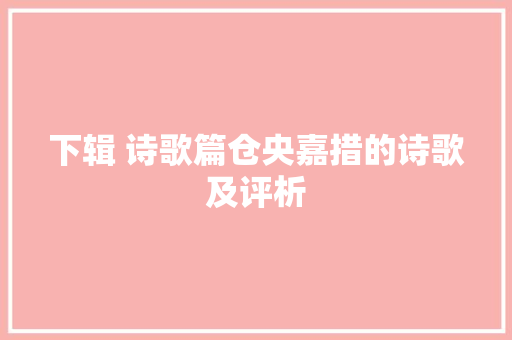
笔者编辑本书的目的,是想给仓央嘉措一个合理的评价,并匆匆成他在近代史上有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这里紧张选编了流传甚广的几个版本(流传的版本之中,多以“情歌”而非诗歌来称呼仓央嘉措的诗集),汇编的资料紧张是便于读者欣赏、查找和对照;同时,笔者在编辑这些诗歌时,根据自己的喜好作了些点评,权当是我个人的“读书随笔”吧,仅供读者参考。
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见笔者最近的两首短诗:“雪域诗圣,莫测修证;以歌传道,广宣法音。”、“一代诗王,半生沧桑;隐姓埋名,默化洪荒。”
②根据我国著名措辞学者贾拉森教授的说法:“‘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玉轮;娇娘的脸蛋,浮现在我的心上。’……原文可直译为“未生阿妈的脸庞(脸的敬语)”。刘家驹、苏朗甲措、周良沛尊重原作,翻译基本准确;于道泉译文精确,但加了一个多余的“指少女”的表明”(《从仓央嘉措一首诗看仓央嘉措诗歌的所谓的“情”》)。
弁言一:以歌传道知多少?读中国文学史可知,中国诗歌源出《诗经》、《楚辞》,而后经汉乐府之流变,至唐而看重对仗格律,于是中华诗歌繁荣至极;至两宋而有词之创新,且成时尚,因而唐诗、宋词遂成中华文学的两大奇异风景;后有元曲、清对联,是为中华文明一脉之相承。故古人呤诗为难刁难、写(羊毫)字作画,定是人生必修之课。在唐、宋诗歌艺林中,佛教的禅诗影响较大,霸占极为主要的一席。故禅诗虽不敷以夺李、杜、苏、黄等人之席,但同样也是诗中的别调。据不完备统计,唐宋期间的禅诗大致在三万首以上。
在我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期间——唐代及稍后一段韶光里表现尤为明显。唐至五代,有据可查的僧人诗集就达40余部,涌现了以王梵志、皎然、齐己、贯休、寒山、拾得为代表的一批诗僧,诗作丰富,造诣斐然。又如,大墨客李白所作之《赞佛偈》(即“稽首天中天,光线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在佛教中流传很广,他还因晚年喜好学佛参禅,自号“青莲居士”。举凡王维、苏轼、黄庭坚、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墨客或大文学家,多与佛教有甚深交往某人缘,可见佛教影响之巨,故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基石是有根源的;有的乃至出家为僧,或从僧返俗,如近当代的太虚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苏曼殊、清定上师、隆莲尼师等,这些佛教高士,其才华与背景让人读罢总是让你佩服和冲动的。再如,宋代著名禅师普明所作的“牧牛图颂”可谓禅诗中佼佼者之一,正如古人评论他:其诗“言近而旨远”,其图“象显而意深”一样,深受广大学者或参禅者所保重,唱和者亦代不乏人,乃至远至日本;酬唱之作达二百余首,如此数量在诗歌史上实属罕见。
以歌传道的方法,自古以来都很盛行。古时,因无笔墨,又无纸张,以是文化传承全靠口耳相传;而为了便于影象,每每采纳对仗工致、音律押歆的诗歌办法相授,于是就有了诗歌或戏曲,如古印度的《四畎陀》、中国的《诗经》等。佛教中则有更多的例子,如《六祖坛经》中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多人都能耳熟能详;又如南北朝·齐·傅翕(傅大士)的《心王铭》、唐·玄觉(永嘉)禅师的《永嘉证道歌》、宋·普明禅师的《牧牛图颂》;再者,如西藏的《米拉日巴尊者歌集》、《仓央嘉措诗歌集》等,这些作品都流传千古、随处颂扬的著作。
在此,笔者摘录一些禅宗著名的偈颂或禅诗,以供读者欣赏、阅读,若能从中得悟人生究竟,或开拓心胸,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若能从中参透佛理,从此对人生有了更深层的体悟,或增加正见、或增益聪慧,笔者当随喜祝福,于所祷!
正如曾缄师长西席所说的那样:“仓央嘉措既长,仪容玮畏,神采秀发,赋性通脱……仓央嘉措学瞻才高,在诸世达赖中最为精彩,故屡遭折辱,犹为藏人爱戴。”、其“歌曲流传至广,环拉萨数千里,家弦而户诵之……”、“情辞悱丽,余韵欲流……诚有令人动魄惊心者也。……故仓央嘉措者,词坛之元勋,言情者之所归命也”、“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出身”可见他的诗歌极具魅力,称其为“雪域诗圣”实在是名副实在。
后世的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对其评价为“六世达赖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天下,他的诗歌和歌曲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用最诚挚的慈悲让俗人感想熏染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领受到了真正的教益!
”可以说是代表了不少藏传佛教信众的心声,他们对六世达赖始终保持虔信和敬仰的心,丝毫没有疑惑与轻渎之念,从中即可突窥见仓央嘉措过人之处!
白玛僧格于清心斋
2011-8-20
————————————
注释:
①见笔者最近的两首短诗:“雪域诗圣,莫测修证;以歌传道,广宣法声。”、“一代诗王,半生沧桑;隐姓埋名,默化洪荒。”以及信理所著《关于仓央嘉措结局四种说法的辨析》一文。
②根据我国著名措辞学者贾拉森教授的说法:“‘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玉轮;娇娘的脸蛋,浮现在我的心上。’……原文可直译为“未生阿妈的脸庞(脸的敬语)”。刘家驹、苏朗甲措、周良沛尊重原作,翻译基本准确;于道泉译文精确,但加了一个多余的“指少女”的表明”(《从仓央嘉措一首诗看仓央嘉措诗歌的所谓的“情”》)。
③吠陀,梵Veda,巴Veda,藏Rig-byed,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根本圣典的总称,也是现存印度最古的文献群;音译又作韦陀、围陀、毗陀。“veda”一语系由动词“vid”(意为知)所衍生的名词,意为知识——尤指宗教方面的知识、神圣的知识,后来转指宗教知识方面之文献,此类文献的成立与婆罗门教的祭仪有密切的相干。吠陀文献原有三种,即《梨俱吠陀(Rg-veda)》、《沙摩吠陀(Sa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个中,(1)《梨俱吠陀》系赞歌之结集,成立最早,约在西元前1200年前后。(2)《沙摩吠陀》系配有一定旋律而吟唱的歌词集。(3)《夜柔吠陀》系举行祭仪时所诵咒文的集录。此三者总称为“三吠陀”(或三明)。此外,另有《阿闼婆吠陀》,系禳灾招福等咒词之集成。此种吠陀与民间崇奉有深切关系,原不具有吠陀的正统身份,到后来才得到“第四吠陀”的位置。此上四种吠陀逐一皆包含本集(Samhita)、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nyaka)、奥义书(Upanisad)等四部分,但常日在言及吠陀时,大多单指“本集”而言。又,相传这些吠陀圣典系古印度的圣仙、神祇的启迪而作,故又称为“天启(Sruti)文学”;吠陀最初仅系口口相传,并未形诸笔墨,后来才用以比古典梵语更为古老的吠陀语(Vedic)写成。因此,此类文献是学术界理解古代印度宗教、文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而且对付当代印度人的精神生活仍具有甚大的影响。
④梵书,梵名Brahmana。音译婆罗门那,是阐明婆罗门教吠陀圣典之文献。吠陀,狭义指四吠陀之本集(梵Samhita);广义则合本集及梵书(广义),总称“吠陀”。梵书为婆罗门教奠定了吠陀天启、敬拜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吠陀本集包括祭仪时读诵之赞歌、祭词、咒词。梵书亦有广义、狭义之分:规定祭仪之实践方法,或阐明赞歌、祭词之意义,解释敬拜之起源、秘义者,属“广义之梵书”,其内容可分为梵书(狭义)、森林书(梵Aranyaka)、奥义书(梵Upanisad)三部分;这个中,梵书(狭义)又分仪轨(梵vidhi)与释义(梵artha-vada)二部分;仪轨,为规定敬拜之顺序方法、赞歌之用场等;释义,则讲授赞歌之意义及语源、敬拜之起源及其意义等。森林书及奥义书则同为稽核敬拜及人生之意义,二者均重理论;个中,奥义书尤深探哲理,又特名为“吠檀多(梵Vedanta)”。梵书,因此散文体裁书写成的、有大量之神话与传说的篇章。梵书之成立年代约在西元前一千年至六百年,即雅利安人由婆罗门文化中央之印度河流域东移至恒河平原时,乃吠陀祭仪繁芜体系完备整备之时期产物。
⑤奥义书,梵名Upanisad。音译作优波尼沙土。为古印度之哲学书。系以梵文书写,为师徒对坐密传教义之书本,故称“奥义书”,为记述印度哲学之原来思想。印度之宗教始于对吠陀之赞颂,其后以解释用法与仪式为目的之梵书兴起,个中有一章名之为“阿兰若迦(梵Aranyaka)”,奥义书即为解释此章而编述。阿兰若迦之说幽微,取森林遁世者所读诵之义而名之为《森林书》,特重形式与神学方面,而奥义书则与之相反,属于纯洁哲学。其以阐释吠陀终极意义为旨,连续吠陀末期之哲学思想,发挥新见地,此部分又称吠檀多(梵Vedanta)。原意或为吠陀之末了部分,后转解为吠陀之究竟意义,其后之发展特受重视,成为后代各派哲学之根源。后来传本多达二百余种,紧张者有十数种,总称《古代奥义书》,完成于纪元前八百年至纪元前六百年。此后十数世纪,仍有陆续增长之作,称为《新奥义书》。以文体而言,分为古散文、散文、新散文三种,自古被视为“天启文学(梵Sruti)”,为印度正统婆罗门思想之渊源,亦为印度后世哲学、宗教思想之典据、紧张根源。以文体而言,可分三类:(1)古代散文奥义书:《Brnadaranyaka》、《ChandogyaKausitaki》、《Aitareya》、《Taittiriya》、《Kena》。(2)韵文奥义书:《Isa》、《Katha》、《Kathaka》、《Svetasvatara》、《Mundaka》。(3)新式散文奥义书:《Pra'sna》、《Ma-ndukya》、《MaitriMaitrayana》。本书译本极多,最古者为波斯译本,其后有拉丁译、德译、英译、中译、日译本等。
⑥薄伽梵歌,梵名Bhagavad-gita。又作圣婆伽梵歌,意译为“世尊歌”,为古代印度之宗教诗,即《大叙事诗》(梵Mahabharata,音译摩诃婆罗多)第六卷毗须摩品中第二十五章至四十二章部分。其作者与著作年代不详,约作于西元一世纪旁边。或意译为“神圣之神歌”,为印度教毗湿奴派之圣典,至今全印度教徒仍视为圣典而普遍读诵。内容紧张摄取数论、瑜伽、吠坛多三派之哲学思想与伦理不雅观念,鼓吹通过修练瑜伽,使个体灵魂“我”及宇宙灵魂“梵”相结合,以达到分开死活循环之最高境界(涅槃)。即藉由阿耳柔那王子(梵Arjuna)与毗湿奴之化身吉栗瑟拏(梵Krsna)之对话,强调无执着之行为是人类唯一应尽之道,依正智而发展出智行合一思想是趋向解脱之道的聪慧方法;而易行之解脱道,则端赖于对唯一神之绝对信爱(梵bhakti),此说遂成为毗湿奴派发展之起源。印度教哲学思想之发展,便是常以注释薄伽梵歌之形式涌现。
⑦罗摩衍那,梵Ramayana,又译《罗摩传》、《罗摩延书》,为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此诗之篇幅较另一史诗《摩诃婆罗多》小,全诗有二万四千颂,分为七篇。相传作者为伐尔弥吉(Valmiki,蚁垤神仙),但事实上,伐尔弥吉应只是编纂者而已;全书绝大部分完成于西元前五百年至三百年之间,而第一篇与第七篇则成立于西元二百年旁边。在这较晚出的第一篇与第七篇之中,含有甚多神话与传说,并且由于将历史人物的罗摩当作是毗湿奴神的化身,乃使此一史诗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世遂有‘罗摩崇拜’的环境发生,颇为近代印度教添放异彩。全书七篇,阐述憍萨罗国(Kosala)王子罗摩,因遭嫉而被放遂十四年;后来,为拯救被魔王掳走的王妃息妲,乃远赴楞伽岛与魔王大战。末了,大败魔王,夫妻团圆并且返国为王。书中故事过程弯曲离奇,人物角色忠奷分明。其文体远较《摩诃婆罗多》洗练,词汉文雅,是后世印度美文体(kavya)作品的来源。本书目前在印度有三种异本传世,即:流布本、孟加拉本、西北印度本。书中的故事不仅被改编为古典梵语文学作品,更被翻译为印度各地之方言,以及英、日、德、爪哇、马来亚、泰国、中国等国笔墨。
⑧摩诃婆罗多,梵名Mahabharata,意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又称婆罗多书、大战诗。为古代印度之民族大叙事诗。以梵文书写,计有十八篇十万颂附录一万六千颂所合成。其份量为另一叙事诗《罗摩衍那》的四倍,为天下最长之史诗。与《罗摩耶那》并称印度二大史诗。相传作者为毗耶娑神仙(梵Vyasa),或谓其仅为编纂者。纪元前数世纪口耳相传,经多次改动补遗,至西元二百年始得其概要,四世纪时,始完成今日之形式。其主题为婆罗多族之后裔德雷陀什陀(梵Dhrtarastra)与庞都(梵Pandu)两王族为争夺王位,展开十八日之战役。其年代虽不明确,然其战役史实则无庸置疑。
⑨米拉日巴(1040—1123),本名“兑巴嘎”,意为“闻喜”。米拉日巴的父亲名叫米拉协嘉,母亲名叫娘萨嘎坚。米拉日巴1040年(宋康定元年)生于贡塘(今阿里地区吉隆巴县西南)。他的父亲本是后藏贡田地方富商,因喜得贵子,因此给他取名为“闻喜”;后来,他有了一个妹妹。在米拉日巴7岁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当时他的母亲年仅24岁;后来,他的伯父强行夺走了他家的所有财物。如是,他母亲只得与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极其穷苦的生活;等到米拉日巴(即闻喜)终年夜后,就让他出外学习苯教的谩骂之术,以期报仇雪恨。闻喜先到藏绒鲁库隆(今仁布县境内)地方,跟随黑咒喇嘛拉杰鲁琼学习“红面黑面凶曜法”(苯教的一种咒术),学成之时,恰好他的伯父雍喜正给儿子娶妻举办结婚宴会,于是他用咒术让房屋溘然塌陷,压去世了35人,仅留其伯父和伯母未去世。后来,他又从雅隆喇嘛雍敦绰嘉学得了“放雹法”,那一年的快秋收时,闻喜在一山谷中筑坛作法施放雹术,砸毁了全村落所有的庄稼;当他看到人们捶胸顿脚、哭天喊地的惨状时,善根大发,深深后悔不该杀人、毁稼,于是决定弃“苯”学“佛”。后拜洛扎(即妥普曲切城)高僧玛尔巴(1012—1097)为师,这一年米拉日巴38岁。开始,玛尔巴开始并不教米拉日巴任何密法,只是命他在四周山坡上修建屋子和许多耕种苦活,他因常常背负石块,背部被磨破而流血化浓,但仍勤恳不已,毫无怨言。玛尔巴故意让他经历了受六年的苦行折磨,经历了“八重”磨难,以洗他前半生所造下的罪业,之后才传授他密法。玛尔巴将所有的教授与密法完全的、正式地传给了米拉日巴;又让他从卓波隆上区来到达纳普(黑马岩洞)中闭关专修。就这样,米拉日巴在师尊前先后修行了近7年。45岁那年(1084年),他回到家乡探亲,才知道母亲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妹妹讨饭也不知道去向。悲哀之下,米拉日巴遂到阿里地区隐居潜修,长期以野荨麻为食,刻苦精勤,前后潜修了9年,终得大造诣,得到“风息(密乘所说“体内”、“明点”、“脉”三者之中的生命元素)清闲”功能,末了终于即身证得了“最胜悉地”(梵文音译,意为“造诣”)。听说这种功能会使人升在空中,并能在空中自由行走。从此往后,他四处云游,以“道歌”形式鼓吹教义,遇有缘弟子请教授密法,著有著名的《道情歌集》行世。从学的人很多,弟子中得“瑜伽”造诣者多达百余人,以“热琼巴”、“岗波巴”二人最为精彩。他是宋代西藏著名的佛学家、苦行僧;他也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从古至今,他被全西藏信众认可为“即身成佛”的典范,被誉为“西藏密宗造诣第一人”。
⑩《历代词话》清·王弈清
⑾《文心雕龙》五十卷,[南朝·梁]刘勰
⑿《左庵词话》清·李佳
⒀《第三只眼看青藏:青藏铁路采访条记》,杨越/著,2006.9
⒁见中国青年报刊载的《仓央嘉措——一贯被误读,从未被理解》一文,转载悛改华网,2011年01月18日
⒂《关于仓央嘉措结局四种说法的辨析》信理/著,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