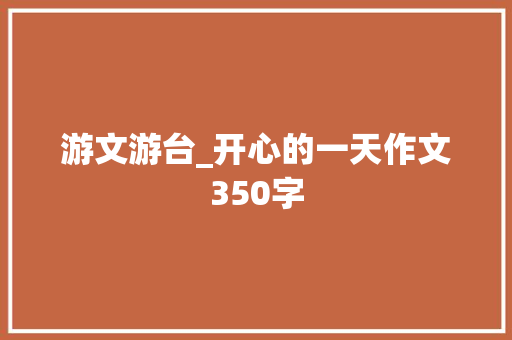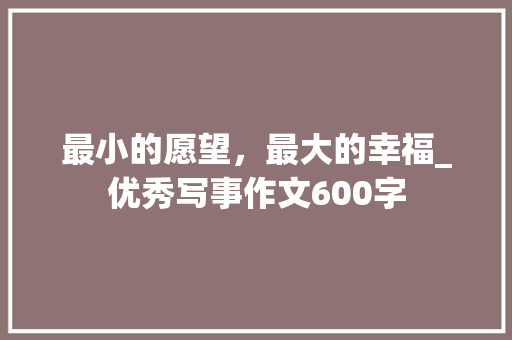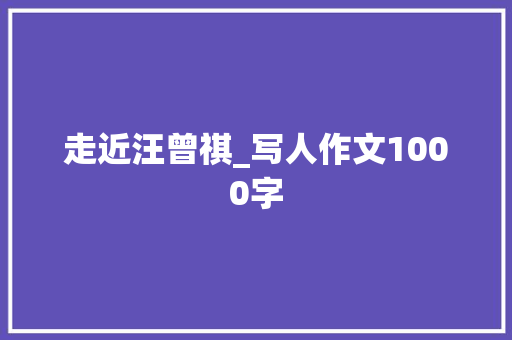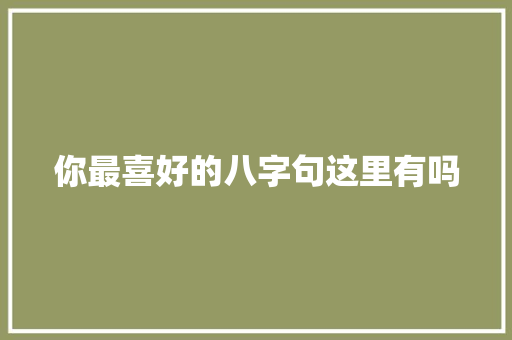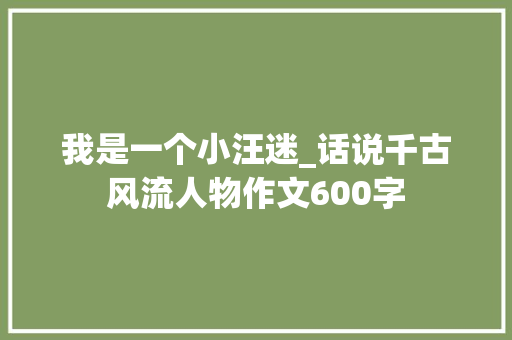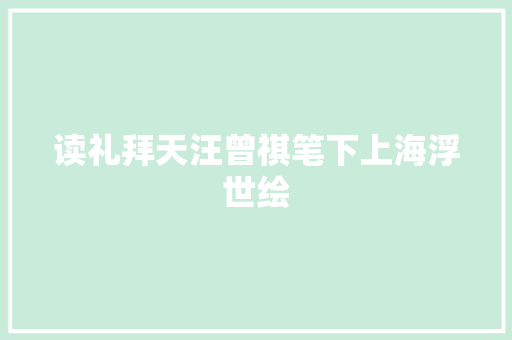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怀的人性主义者,中国末了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末了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造诣,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研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来源百度百科)
【汪曾祺散文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构造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朴实,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眇小零散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伟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措辞,反拨了笼罩统统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蕴藉节制的阐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散的古典主义的绅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壁,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看重不雅观念的贯注灌注,但发人寻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个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管苦瓜到接管,末了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当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便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来源百度百科)
汪曾祺行文古意很浓,比如讲喷鼻香瓜的第16自然段,基本上便是古文句式,以是整篇转译下来,阻力并不大。但同时原文的恬淡雍容已经渗透到字词句篇的各个方面,想要用古文呈现一种不同的风貌,难度反倒加大。
夏天
夏晓怡人。空气风凉,草叶悬露,手书一张,口诵一篇。甚为快哉!
凡花多五出,栀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粗大色白,近蒂微绿,喷鼻香极而冲心脾,吾村落夫谓:“触鼻喷鼻香”。素无纤巧兼盈俗馥,遂为雅人不取,以其格庸。栀花曰:“我去!
吾喷鼻香此喷鼻香之畅快,与汝何干!
”
人向以栀花比之白兰花。吴女卖花串巷,娇声呼曰:“栀子花!
白兰花!
”白兰花半开而娇嫩,牙白喷鼻香静,略甜俗,为沪“怡红院”之“艺伎”所喜,盖因有云白兰花置夜枕则弥喷鼻香。与其艺伎枕上,不若船姑髻边。
夏花最幽寂者莫过珠兰。
牵牛花易凋。晨露初开,过午而萎。
秋葵命薄。瓣黄,蕊白而围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
凤仙花有单瓣,有重瓣。重瓣如小牡丹,花茎粗肥,湘人用之以腌“臭咸菜”,此吾乡所未有。
马齿苋、狗尾草、益母草, 花叶茂盛。
淡竹叶开蓝花,如小蝶,甚好看。叶略似竹而稍软。
“万把钩”即苍耳。小果多钩,触之则挂衣,仔细摘去。童蒙谓之“万把钩”。
又有“巴根草”,贴地而生,见缝扎根,一株蔓延,密织一片。坚韧顽强,牵扯而不断。童谣曰:
巴根草,
绿茵茵,
唱个唱,
把狗听。
最恶者乃“臭芝麻”。捕蟋蟀、捉金铃,常沾一裤管。其臭无比,甚难除净。
西瓜以绳络悬井中,下午剖食,刃,喀嚓有声,凉气四溢,直扑眉眼。
天下皆重“黑籽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以东墩产者最佳。
喷鼻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色淡绿,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肉脆,京城亦有,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喷鼻香;梨瓜,大如拳,皮白,白瓤,生脆有梨喷鼻香;又有较大者,皮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童谓之“奶奶哼”,言奶奶边吃边“哼”。
蝈蝈,吾乡谓之“叫蚰子”。一种曰“侉叫蚰子”。乃真“侉”也,叫驴般,呕哑烦人。若饲以椒,吵益甚。一种曰“秋叫蚰子”,碧如翡翠,玲珑小巧,鸣声柔细。
勿扰,金铃子爬行于玻璃小盒中矣!
不雅观其止,食两小骰块状鸭梨。遂“丁铃铃铃”鸣叫而起……
纳凉。
置竹床于天井,横竖而卧,身爽暑消。看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甚美。月周有晕,谓之“风圈”,近日有风。“乌猪过江”——黑云漫天河,将大雨。
至于露下,竹床栏杆尽湿,乃归,是时既困,才沾藤枕,已然梦乡。
鸡头米老矣,新桃核熟矣。
夏,亦往矣。
转译|李奕涛
2017年8月9日 于国立樱花大学今聊斋
图:窗外(拍照 湖南 罗素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