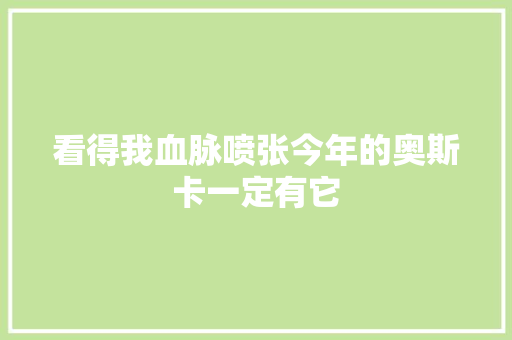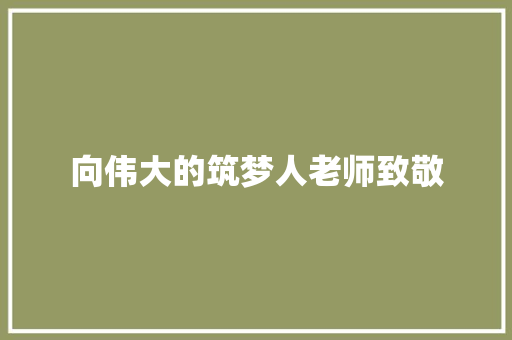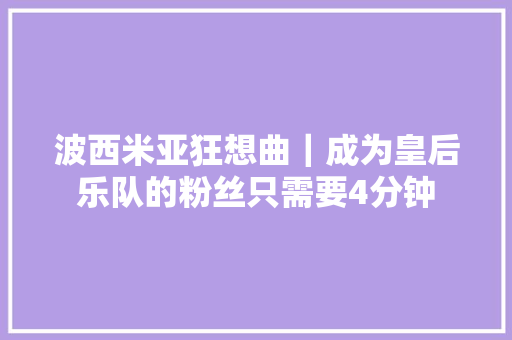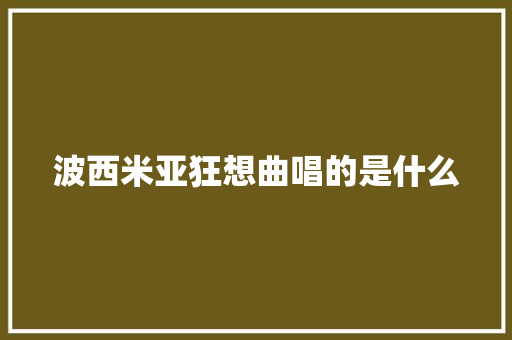《入夜的声音》,作者:[莫桑比克]米亚·科托,译者:金心艺,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与国族时期共振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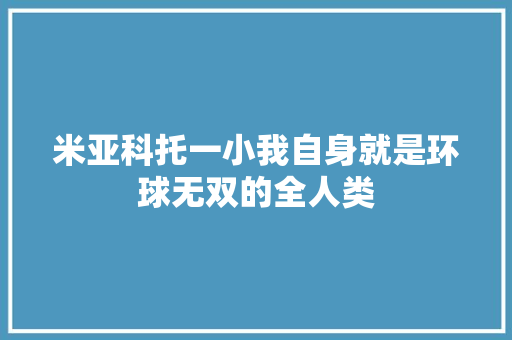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莫桑比克深陷于非洲大陆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内战之一(1975—1992),如米亚·科托所述:“数不清的岁月里,炮火在莫桑比克的地皮上倾泻着哀痛。……只剩下灰烬和溃败,人们失落去灵魂。统统都变得沉重……”和非洲很多国家一样,当时的莫桑比克经历了“后殖民乌托邦”的幻灭;内战和严重的贪污腐败等政治及社会问题,进一步将其卷入新的主体性危急。而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探索政治表象背后社会及伦理繁芜构造的手段,此时却表现出某种局限性,解放战役期间(1964—1974)盛行的文学主题,如国家独立、革命、激进的阶级斗争、黑人性、种族对立及压迫等,彷佛已不敷以用来书写莫桑比克社会的新现实。
因此,当米亚·科托的《入夜的声音》及之后的几部作品问世,立即为莫桑比克叙事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转向。在一个个短小精悍又光怪陆离的故事中,米亚·科托既书写战役与日常、传统与当代、秩序与混乱、贫穷与生存,也大胆触及种族共存和文化交融等过去不容磋商的主题,只管很多时候,对它们的书写充满挣扎与对抗,乃至不乏悲剧性。同时,这些小故事还穿插着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交互、身份与性别议题、生物多样性与冲突,以及对历史与影象如何塑造个体认知的思考。更主要的是,它们生动展现了莫桑比克的众生百相和普通人极为私密的个体情绪履历。可以说,米亚·科托的短篇小说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险些可以看到其日后长篇小说的绝大多数主题。但前者写得更自由,也更具象,由于对小人物来说,每一天详细而噜苏的生活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
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莫桑比克最主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为《梦游之地》《耶稣撒冷》《母狮的后悔》等。
鉴于米亚·科托短篇小说主题的繁杂,读者能清晰地感想熏染到一种与国族时期共振的书写。《入夜的声音》一开篇就将读者拉入莫桑比克要地本地深处的偏远地区。丛林边缘,一对晚年夫妇因战役和贫穷而与世隔绝,被韶光与当代社会所摈弃。“在这片孤独的荒地上”,生命萎缩到只能思考如何去世亡,去世亡却“只是一次大略的滑行,抑或翅膀的紧缩,不像在别处:生命熠熠生辉,去世亡是一场暴烈的撕扯”。对付熟习米亚·科托作品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场景一定不会陌生,由于无论是《梦游的大地》(1992)开篇那条被战役杀去世的道路,还是《缅栀子树下的露台》(1996)中那座只有父老收容所的孤岛,抑或许多作品中那些偏僻而无知的小村落镇,彷佛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里被贫穷和去世亡的阴影长久笼罩,梦想与希望也几近消亡。蛮荒之地,是米亚·科托用来呈现战役期间与战后莫桑比克人生存情状的基本场域。而“入夜的声音”,实际上指无数堕入荒地和暗夜的个体,他们之以是“黯淡无光”,是由于共同承受着后殖民期间的暴力与精神创伤,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同时,或麻木,或猖獗,或残酷,或为幻梦和伤痛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是,《入夜的声音》是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最沉郁阴郁的部分。米亚·科托为这一期间莫桑比克人的精神状态写下了这样的注脚:“贫穷最令人酸心之处便是它对自身的无知。面对空空如也的情状,人们弃绝梦想,失落去成为另一种人的渴望。虚无中存在着一种圆满的幻觉,它让生命停下脚步……”
揭橥于1994年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被赐福的梦中故事》,则明显有着更加通亮和温暖的色彩。此时内战已经结束,莫桑比克规复和平,如同一场漫长的酷烈干旱,终于迎来歌声悦耳的大雨。在故事《被赐福的梦中雨》中,“我”注目着下雨的街道,“彷佛坐在全体国家的窗边”,相信“地皮这位贫瘠的原住民,将会逐渐得到斑斓的美”。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的故事里,去世亡依然无处不在,暴力也并没有消逝,悲剧仍在上演;但同时,生命也变得更加鲜活和丰裕了。米亚·科托将这种变革归因于人们开始有梦和希望:“梦隐匿在我们内心最难以抵达的地方,那里,暴力无法出击,野蛮无路可走。”被梦的雨水浸湿后的“声音”,有了穿越“去世寂”、迁离蛮荒之地的力量,纵然身处黑夜,也可以“化为月光,长久存续”。
消解二元对立的单一界定
莫桑比克最伟大的墨客若泽·克拉韦里尼亚(José Craveirinha, 1922—2003)曾经将米亚·科托的长篇处女作《梦游的大地》喻为一幅巨大的“民族马赛克”。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科托的短篇小说集。在科托看来,莫桑比克本便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群体构建起来的多元民族社会空间。现实的沃土授予他笔下的人物无尽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无论是稽核单个故事,还是超过不同故事,我们基本都看不到雷同的角色。有些人的职业或生活千差万别,例如想读书的放牛娃、望女成凤的小镇机器师、爱而不得的捕蛇师、集市里谈笑风生的理发师、与石像谈恋爱的驼背女;有些人职业相同,命运却截然不同,例如《神鸟》和《盲渔夫》中的两个渔夫。乍一看,许多人物可以直接代表莫桑比克社会各个族群,例如《梦见飞鸟的猴面包树》中的原住民和殖民者,《俄国公主》中的黑人同化民与白人移民,《众神广场》《聋神父》与《去世亡占卜师》中的穆斯林、基督徒和本土巫师,而自挖双眼、出海生还后在沙滩上探求面孔的渔夫,仿佛便是在时期的浪潮中探求自我的莫桑比克。很多时候,人物又表现出偏离其类型标签的非范例性,例如《梦见飞鸟的猴面包树》中,白人殖民者的孩子全心全意地亲近原住民,末了在烈火中,与象征黑非洲传统的猴面包树融为一体。
关于身份,科托的基本态度是谢绝并消解统统指向二元对立的单一界定。在《卡洛塔·让蒂纳,原来你从未飞过,对吗?》中,主人公对状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许多个伤心人。……要不这么说吧:我们是一个伤心人?”(Eu somos tristes. [...] Ou talvez: nós sou triste?)这在葡语中是一个大略的笔墨游戏,即将本该保持单复数同等的主语“我(eu)/我们(nós)”和谓语动词“(我)是(sou)/(我们)是(somos)”进行错位搭配。由此,故事的开场白既表达了个体身份内部的多重性和复数性,又强调身份从个体转向集体的可能,即共有的经历或情绪可以使人们产生共鸣和某种归属感。非洲葡语作家八九十年代的身份书写,每每会被纳入后殖民理论视阈下“糅杂性”(hybridity)观点的谈论。但在米亚·科托早期的短篇小说中,“糅杂性”并不仅仅指殖民地历史和后殖民期间文化、身份或意识形态的流动与混融状态,它也是人类作为万千物种之一所固有的特点。正因如此,科托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每个人都是一个种族”才尤为耐人寻味。作者借卖鸟人之口发布,“我便是自己的种族。一个人自身便是独一无二的全人类”,既强调个体具有独特而完全的属性,无法只纯挚归类于任何现有的种族或群体标签,是身份多样性的明证,又暗示每一个个体都是全体人类的缩影,其生存与情绪经历亦可表示身份与存在的普遍性。
然而,对付一个亟待以“我们”来建立集体身份认同,从而夺回完全主体权利的族群来说,内部同样存在对差异性个体的冷漠与歧视,仿佛只有去除“杂质”,才能得到一个“纯粹”的主体。在《甜脸玫瑰,罗莎·卡拉梅拉》中,米亚·科托塑造了一个因自身的糅杂性而被本该收受接管她的社会群体残酷排斥的人物:驼背女。科托在设计她的名字时借鉴了生物学的“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属名在前,种名在后,后者润色并限定前者:罗莎(玫瑰)·卡拉梅拉(甜脸)。但讽刺的是,生物学上对物种身份的承认,在故事中却成了集体对差异性个体履行排他和霸凌的手段。驼背女的悲剧揭示了“二元对立”思维在任何一种身份构建过程中的暗藏性和无孔不入,也提醒读者,个体的繁芜与多样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浸染下的一定结果,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原谅。
在米亚·科托笔下,身份是一种永恒流动、不断变革与发展的叙事。这一点在那些徘徊于死活之间的人物身上,无疑最为明显。科托非常善于描写各式各样的“阴阳人”,比如与生者一起生活的去世人阿巴多·萨兰热,能够与去世者互换的活人占卜师,被村落民认定去世亡的两个重现者,影子被杀手收割的药草科学家,等等。生者与去世者的身份不是在客不雅观事实上发生转换,便是在他人眼中与事实形成倒错。一方面,对去世亡的敬仰是莫桑比克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只有不遗忘去世亡,才能记住历史,拥有影象才能实现身份叙事,不敬仰去世亡(没有影象)者则不能称之为人。另一方面,死活的流转以及随之而来的荒诞感,是很多读者认为科托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紧张缘故原由之一。但正如科托本人及其各国译者和研究者反复强调的那样,他的故事里并没有所谓的“魔幻”,有的只是个体眼中所看到的天下,他们对生活的具象感想熏染,决定了我们读到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容貌,有着若何的逻辑。因此,当公牛马巴塔-巴塔爆炸时,“血肉变成赤色的蝴蝶”,骨头成为“散落的硬币”,这样的画面在一个并不真正清楚作甚去世亡的牧童眼中,无疑便是最真切不过的现实。
身份的流动与个体对天下的感知是相辅相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米亚·科托乃至在叙事空间上也强化了流动的特质。他的短篇小说中会大量涌现河流、海洋、雨水、行舟等具有高度流动性或移动性的象征物;即便在没有水流的地方,科托也会创造出一种过渡性空间,如窗户、露台、阳台、走廊、屋外的台阶甚年夜公路等,使人物得以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穿梭到一个更广阔的天下。莫桑比克是一个传统上笃信万物有灵的国家,个体在这样的宇宙不雅观和生命不雅观影响下,总是渴望与他人以及非人类或精神性的“余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走出自我的牢笼。在科托看来,个体须要融入天下,自我必须成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不断延续身份的探索和构建。
冲破叙事文学和诗歌的边界
在《热格叔叔的私人启迪录》中,主人公坦言:“我们总是讲不好某个人的故事。由于人每时每刻都犹如新生。没有人的生平是单一的,每个人都会分解成各不相同、不断变革的人。”但米亚·科托是讲故事的妙手。他的短篇小说最大程度地领悟了各种形式的民间元素——起源神话、种族传说、习俗传统、社会新闻、社区八卦、箴言警句,再由叙事者以丰富的口述办法,将事宜娓娓道来。有时,叙事者会借自白或告解来讲述亲自经历的故事,或者化身为人群中的好八卦者,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用非线性叙事拼凑成不完全的画面;有时,叙事者又隐于文本之外,闇练引用“新闻宣布”,条理清晰地展开一个故事。但无论如何,读者总会创造, 有一个小人物,在一个看似平凡的环境中,陡然进入一个现实与抱负交叠的离奇情状,经历不可思议之事,故事会以出人意料的办法戛然而止,但又彷佛没有真正结束;有些故事中,人物一开始就透着古怪,可他们说话干事的办法却再自然不过,仿佛统统都是天经地义;而一个客不雅观上已经消亡或无疾而终的事宜,米亚·科托又总能为其披上诗意的想象,使之拥有延续与开放的可能。就这样,米亚·科托用短篇小说这种高度凝练的叙事文体,写下一个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寻衅乃至颠覆读者的理性或惰性期待,反复操练着读者理解莫桑比克当代现实的能力——这种现实,是事实与想象的高度领悟,是超越常规而尚未被莫桑比克人完备节制的生活与情绪体验;而米亚·科托期待读者具备的能力,是一种不拘于既定边界和知识局限的诗性感想熏染力。
米亚·科托是一个写小说的墨客。他曾在文章中表示:“写作总是须要诗意。诗歌是另一种思维办法,超越了学校和当代社会教给我们的那套逻辑。它是另一扇打开的窗,让我们以新的眼力看待生命和事物。”科托非常强调要从“凌乱无章的言语、措辞和叙事模式”中创造“美”——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聪慧,或者一套自由而不安分的措辞符号系统,始终游离在确切的语义周遭,不断试图更新措辞所要表达的意义。措辞的构成无疑是多层次的,因而科托不遗余力地在各个维度创造打破语义边界的诗性年夜水,一如他为叙事空间创造流动的自由象征物那样。科托早期的叙事作品中,“造词”是非常经典的诗性写作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本土方言与葡萄牙语的糅杂、既定葡语单词的衍生、多个词语的粘合或混成等。当然,在词语单位之上,还有对葡萄牙谚语、俚语的创造性改装,本土谚语和俚语的虚构,以及诗歌、书面叙事措辞和本土口语在同一个创作阶段中的对抗与磨合。
科托的“造词”每每多义且开放,个中,衍生词和混成词最能表示语义的流动性。在我们的选集中,“入夜的声音”(Vozes Anoitecidas)与“被赐福的梦中故事”(Estórias Abensonhadas)两个标题就包含了衍生词和混成词。“Anoitecidas”的原形是“夜幕降临”(anoitecer),后者在葡语中本是无人称动词,但科托将其衍生为被动语态的过去分词“anoitecido”,再用其形容词性功能来润色“声音”(vozes),从而通报出两层含义:“夜晚的声音”以及“被卷入夜晚(或被夜幕笼罩)的声音”。另一个标题中的“abensonhadas”则先是稠浊了动词“赐福”(abençoar)和一系列与“梦”干系的词,如名词“梦”(sonho)、动词“做梦”(sonhar)、过去分词“被梦见的”(sonhado),再从这个整体衍生出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容性过去分词“被赐福的、被梦见的”(abensonhadas),来润色“故事”(estórias)。用不同的措辞翻译这样的笔墨,本身也是一个意义流动和延异的过程,或者说“非韵律认识论”(Stefan Helgesson)之间的碰撞。英语译者翻译这样的词,有时会选择不翻译——隐去该词(如Eric M.B.Becker在翻译“被赐福的、被梦见的雨”时,直接处理成“雨”),或保留原文拼写、让读者自行想象;有时则以某个语义为支点进行改写,例如David Brookshaw就将第一个标题改成了“声音造就夜晚”(Voices Made Night)。对中文译者来说,除非像艺术家那样大造天书,否则用写法固定的汉字,险些不可能还原米亚·科托的造词形态,因而用“非造字”办法来处理“造词”征象,是中文译者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例如在本书中,处理混成词时,如果中文现有词汇本身自带多重含义,可以覆盖原文的意思,则不选择硬造生词或做阐释性翻译,避免行文壅塞或冗长;如果混成词包含的多重含义并置在同一个表达单位中,会因汉语自身的语用习气、文化习俗、自然环境(如涉及汉语环境中并不存在的动植物)等成分造成表述逻辑断裂,则在原词中选择不那么随意马虎造成阅读障碍的含义进行翻译,或将原词的多重含义拆解,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文表达单位中去,乃至以句译词;有时,一个词的混成办法有多种可能,意义也会随之浮动,那就采取音译加脚注(如《帕拉兰的旗杆》中对“帕拉兰”一词的处理),由读者参与解码,完成终极的表意;而当某个无比美妙的时候降临,原文的每一个含义都能在简洁的中文里绽放光彩,译者便可放心地利用“显性翻译”,用另一种诗歌措辞去回馈作者。无论如何,译者须要保持一种信念:既然“造词”是米亚·科托不屈从于边界的表现,那么它也不应该成为译者翻译时的桎梏与生理障碍。事实上,米亚·科托的诗性书写并不纯挚依赖“造词”,而因此无处不在的背叛性修辞为根本,展现莫桑比克人独特的思维办法与天下不雅观,这便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当“造词”已彻底退出科托叙事的舞台,他的笔墨依然能让人一眼认出这便是米亚·科托。阅读这样的笔墨,无论译者还是读者,都须要学会感想熏染新奇,不断重新想象和重塑人的处境。因此,保留并呈现一系列非常规的、“在意义门槛上抖动的(诗性)隐喻”(Grant Hamilton & David Huddart),或许才是米亚·科托最希望他的“互助者”(译者)完成的寻衅。
阿契贝曾经在《非洲文学:“庆典的回归”》一文中提到伊博族艺术殿堂姆巴里神庙的一个传统,即“为人类生平中所有的主要经历,尤其是那些新的、异乎平凡的,因而有潜在危险的经历”而创作雕塑。这是一种“庆典”,实在质在于“对存在的承认”,而非“欣然接管”。米亚·科托的短篇小说亦是这样一种承认“存在”的“庆典”,它冲破叙事文学和诗歌的边界,用完备虚构但又极其可信的言说办法,授予莫桑比刻期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经历以真实可感的细节与情绪,揭示那片地皮上共存的繁芜人性。这些鲜活的生命故事,也一次次让迢遥彼岸的我们“瞥见”别样的生活,从而不雅观照并寻思自我。
原文作者/金心艺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