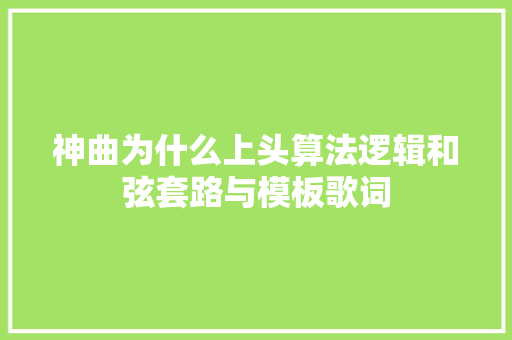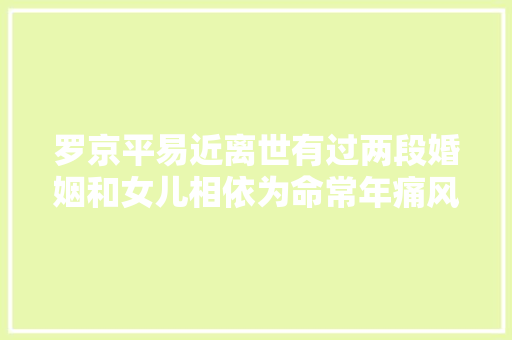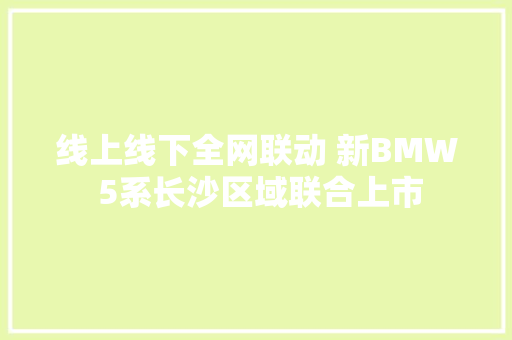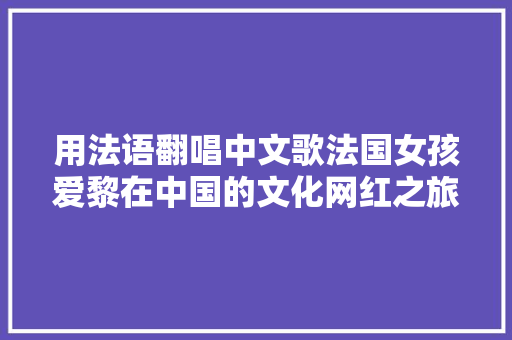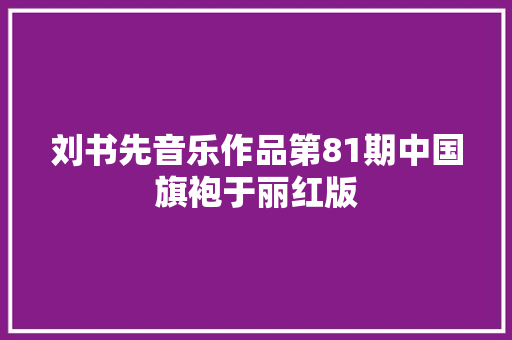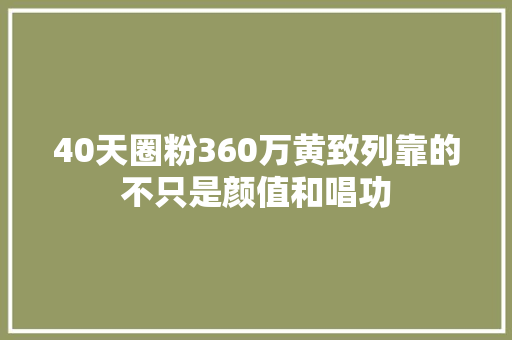精确统计此刻有多少中国血统生活在法国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挨个数清当下有多少法国人正在专一学习中文,历史未必记得第一个来到法国的中国人的样貌,但却将所有第一批中国移民如潜水者一样平常的形象保留了下来,一代代的潜水者筚路蓝缕,积蓄力量将自己的后代助推出海面,成为这片大海中的一名航海者,这些航海者们褪去了生涩与犹豫,继续了灵魂与风骨,凝聚了能量与希望。
2020年下半年的开篇,一场中文歌赛将全天下所有客居异域的“潜水者”与土生土长的“航海者”凑集在同一片港湾,用声音的力量展现新老两辈华人不同的精神天下。在法国,一名已过而立之年的大男人,和一位正值二八年华的小女孩站上了这场比赛成人组和青少年组的终极舞台,他们一个叫王小龙,一个叫蔡天芝。

图 |9月29日,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外洋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联欢晚会在中国国家拍浮中央“水立方”举行。图为中心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宣读成人组银奖得到者名单。
图 |蔡天芝得到法国赛区青少组冠军。
王小龙阴郁萧瑟的《Lost City》是一个潜水者对故土与过往的告慰,蔡天芝刚柔并济的《暗香》是一名航海者对传承和提高的追逐。一场比赛,两首歌曲,将两个并不熟习的人联系在一起,讲述一个有关两代法国华人的故事。
我失落去了我的城市
关于《Lost City》这个歌名该当翻译为“失落落的城市”还是“失落去的城市”,王小龙想了想之后说:“该当说是失落去的城市”,这个常常返国的新疆男人,再也回不去自己的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在王小龙的天下里有两个联系,一个是地理联系,另一个是生理联系,前者是新疆作为家乡的故土情节,后者是与自己在新疆拜过把子的二十几个兄弟的个人情绪。父母自小离异,这些兄弟是王小龙每次返国最大的动力。
图 |王小龙与兄弟们儿时合影的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王小龙的左手纹着美国摇滚乐队林肯公园的Logo,这是他最喜好的摇滚乐队。手腕内侧不大的纹身顺动手臂延伸至靠近肘部,指向肩膀,旁边肩的中央处,隐蔽着他的第二处纹身,这块纹身是他的第一支乐队“第八天”的Logo,这支成立于初中期间的乐队,是他与兄弟们交谊的结晶。“我纹到这个位置的意义便是说,我背负着你们的梦想一贯在前行,但你们在我的背后一贯支撑着我。”
图 |王小龙一共成立过四只乐队,第一支乐队“第八天”由他和新疆的兄弟们在初中时成立,出国后他将乐队Logo纹在后颈,象征着兄弟们的支撑。(受访者供图)
触摸王小龙与自己兄弟天下的正反面一共用了两个下午,第一次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王小龙穿着一件背后印有Comme des garçons的卫衣坐在客厅,阳光从窗户中照射进来,喝着茶说“我以为我们这帮兄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断,从小一起终年夜,最小的从幼儿园和我一起玩,认识韶光最短的也是从高中一起玩的,都是几十年的兄弟了。”
这缕更像亲情,不是交情的兄弟情在《Lost City》的歌词里被展现得很纯洁:“那时的我们都还没有手机,评论辩论的话题永久都是心爱的姑娘和游戏,从来不会在乎下个学期会不会留级,让我们辩论不休的,不过是你抢我的玩具。”这样的回顾王小龙还说过好几个:比如兄弟们骑着自行车到他家,把意欲逃课的他拖下床拉到学校;比如大家去打群架却唯独不叫他,缘故原由是“他们以为我该当更像一个rock star”;比如“第八天”这个乐队名的由来,“那个时候想得比较稚子一些,《圣经》有个传说是神创世有六天,第七天还有个什么,然后我们就说第八天创造了音乐和我们,那会稚子的想法,初高中的孩子。”
图 |王小龙在巴黎与朋友有一支名叫NOASH的中文说唱厂牌,不定期会进行演出。(受访者供图)
第二次是在一个阴雨天的傍晚,王小龙穿着另一件卫衣,坐在开着灯看起来还是有点偏暗的客厅,手边放着一杯加了冰的可乐,阐明着歌词为什么转换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假笑的饭局,虚情假意的表面,暗地里都在学着攀比。”
“逐步随着年事增长,我会创造和之前的兄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也会有这种状态,包括你有时候在群里谈天什么的,会攀比一下自己的车、房、衣服、腕表,我的歌一开始写小时候只会在意心爱的姑娘和游戏,以前不管你买游戏机还是我买游戏机,一帮人都很愉快,由于有游戏机玩了,没有想过那种攀比。”
“我们兄弟有一个群,大家原来也是开玩笑谈天挺嗨的,创造有些人溘然就不说话了,一开始以为他们事情忙,后来创造也不是,后来跟他们开玩笑,溘然有一天我一个最亲最亲的兄弟就生气了,生气了之后我当时很慌,上学的时候他生气了我肯定要和他对骂,但是这次很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哄好他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结果我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特殊特殊堵,把他哄好了,但我更差了。”
图 |音乐之外,王小龙是一名职业拍照师。(受访者供图)
王小龙语速不算快,但肢体措辞变革很频繁,从双手混乱地快速打转到指尖盲目地抠着面前相机的对焦环和取景器,再到末了十指交叉沉着地放在桌上。他在歌词里倔强地写着“反正也没有可能再回到十七八九岁”,但却又看起来像极了一个第一次失落恋的青春期男孩,穿着的那件卫衣胸前写着Need Money No Friends。
“这件事情是点燃我《Lost city》里写这么多话的导火索,让我心里的感情一下就炸了,那几天我脑筋里每天都浮现这些歌词,然后在脑筋里组织组织,然后就这样。”
王小龙今年2月曾将这首歌分享到与兄弟们所在的谈天群里,但在他的印象中“没有人在群里说什么有关紧要的话,也没有人表现出来是不是被触动到”,在此之后他在群里未再说过只言片语,这个曾经在谈天列表中被置顶的群聊如今已被撤下。
我和我的祖国
王小龙2009年出国留学与故土在不经意间越走越远时,出生在法国的蔡天芝只有6岁,父母“在家中电视只播放中文儿童节目”的家规让女儿与中国在不经意间越走越近。
蔡家的弧形阳台可以供应从荣军院到布洛涅森林的宽广视野,站在窗边的蔡天芝穿着一件灰色oversiez卫衣,踮起脚一脸愉快地讲着那些属于中国年轻人的娱乐元素:
“我看过全部的跑男,最近在看密室大逃脱,邓伦胆子小,我最喜好黄...Justin,《极限寻衅》我看的少,我还喜好唐嫣罗晋,《克拉恋人》!
看《锦绣未央》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俩要在一起,后来他俩果真成了。”
如数家珍的样子容貌让她看起来像极了一本正在撰写中的东方小百科,身后窗外的广阔天地彷佛会在某一天无法装下她日益增长的中国知识。
“我们不怕(她)法语学不会,就怕她不会说中文。”坐在阳台茶几旁的蔡爸爸边倒茶边说。
蔡天芝的父母于20世纪尾声先后从中国来到法国,21世纪的第一年,两人相遇结合,组成家庭,出生在父母奇迹打拼期的蔡天芝因此最初由奶奶照料,以是她学会的第一门措辞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法语,而是温州话,后来母亲加入这场措辞教诲接力赛,承担起普通话的教诲重任,等到了入学年事,她的的法语随着学习的深入迎刃而解。
图 |蔡天芝的书架上摆着两本中笔墨典,天芝妈妈说:“这两本字典是我来法国的时候用的,现在交给了她。”(欧洲时报马行健 摄)
“我们两个都会讲法语,但都没有跟她说法语,老师以前怨我们,为什么不在家里教她法语,但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在家里必须说中文,幼儿园那么多小孩,她的法语自然而然会好起来,现在她还会说‘我的中文被你们带不准了’。”蔡爸爸说。
寝室里的蔡天芝唱着李佳薇的《煎熬》,声音穿透墙壁征服听觉,歌单里还有田馥甄的《妖怪中的天使》和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坐在阳台上的父母提及了女儿2017年去北京第一次参加“水立方杯”中文歌赛,那次比赛蔡天芝已经是法国赛区的冠军。
“上次比完赛后,她就说‘爸,我要学(音乐)’,结识了不少爱音乐的小朋友,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了音乐,在音乐学院待了几个星期,我的几个朋友说她高音比较好,有点潜力。”
自此蔡天芝的音乐之路踏上了快车道,巴黎地区大大小小的华人演出舞台都留下过她的身影,2019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巴黎首映时,蔡天芝作为受邀高朋,在现场担当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领唱,谈起那次的经历,蔡天芝说“作为中国人,我很自满”。
图 |2019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巴黎首映时,蔡天芝担当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领唱。(受访者供图)
9月17日登上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赛决赛舞台前,蔡天芝在8月还收成了《超级演说家·正青春》环球青少年演说大赛外洋赛区少年组的一等奖,她演说的作品题目是《最美奇迹》。
在这篇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演说稿中,蔡天芝在结尾处这样说:“中国在与病毒的对抗过程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那是由于中国有太多太多俏丽年夜胆的逆行者。是万众一心,群众联络的结果,民气齐,泰山移,中国对抗病毒的成功,不是奇迹,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只去过北京、温州、泰州和无锡的蔡天芝以前对武汉的并不熟习,以是蔡爸爸的手机舆图里在武汉的位置上放有一颗图钉,用来给女儿先容这个被载入史册的英雄城市在哪里。晚饭时,蔡天芝用叉子挑起盘子里的一根鸭舌放进自己的碗里,被问到往后想不想去武汉时,她抬开始说:“啊,武汉,要去的”,蔡爸爸用筷子指了指盘子,跟了一句“武汉彷佛有个牌子便是做这个(鸭舌)的。”
我们的传承
蔡爸爸是一个好茶的人,阳台的茶几上放着一套不繁芜的茶具,他拿出茶叶放入一只圆润的紫砂茶壶,随后倒入烧开的热水,接着快速将壶中的水倒入茶海,然后再将沸水倒入壶中,少焉之后,壶中的茶水被倒入不大的茶杯,一杯递向坐在自己对面的人,一杯留给自己,杯中的茶还冒着热气,他抿了一口说:“逐步泡,才会喷鼻香”。
蔡爸爸记得来法20多年打拼的很多故事,也记得自己教诲女儿的很多细节,“菜是不可以乱夹的,要么就不吃,要夹就夹前面的,我倒没有打过她(手),但是我会说你要么就吃,要么就少吃点饭,要么你就别吃。”
图 |蔡爸爸的手机里留着为女儿庆祝十岁生日的视频。(欧洲时报马行健 摄)
“将来会遗失落很多东西,你们年轻人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又怎么教下一代呢?”
蔡妈妈说他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吃过很多苦,走过很多弯路,以是“希望孩子不要向我们这么辛劳”,她最想把自己和丈夫身上的干练、担当和任务心传承给蔡天芝,以是四岁的时候就让女儿去参加儿童旅游团,七、八岁的时候送去市政府组织的外出活动磨炼,十一岁的时候这种磨炼更进一步,蔡天芝独自乘飞机去了中国。
图 |疫情期间蔡天芝所在的中文班转为线上传授教化,上课之前,蔡天芝正在练习写汉字。(欧洲时报马行健 摄)
分外的家庭经历让王小龙和妻子这两个都喜好小孩的人暂时搁下了延续血脉的操持,他对传承的想法和他喜好的摇滚和说唱一样大略明了,乃至带着一点极度的味道。
“在我去世后吧,我真的想留下一些东西,不管是一本书,还是几张著名的照片,或者网络上一些你的信息,包括你的歌,这样大家会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过,文化传承要比其他传承更主要。家庭的传承,我奶奶家有三个孩子,我常常和我弟说:‘你哥我是决定不要孩子了,你估计是没得选了’,等往后经历更多了,有机会的话去领养一些孩子,把这份多出来的爱和韶光去给真正须要的人,虽然小时候我有兄弟情,但是我也知道缺失落的觉得。”
练完歌的蔡天芝走出寝室,她的手机壳上写着“忙着精良”,说这个手机壳彷佛以前是妈妈的,接着问我“你是从中国来法国的吗?”,我说“是,大学毕业往后来的”,这个形容自己“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高中女孩一下子又愉快起来,“中国的大学好大,而且还可以住在一起,我也想”,蔡爸爸喝了一口茶,说了一句“能汇聚在一起的,不要散开”,连接寝室与阳台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蔡天芝和妹妹的合影,她在照片中心跳着舞,妹妹坐在地板上举头看着她。(原标题:▶️ “我失落去了心中的故乡”,“爸妈怕我不会说中文”:法国两代华人用歌声讲述发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