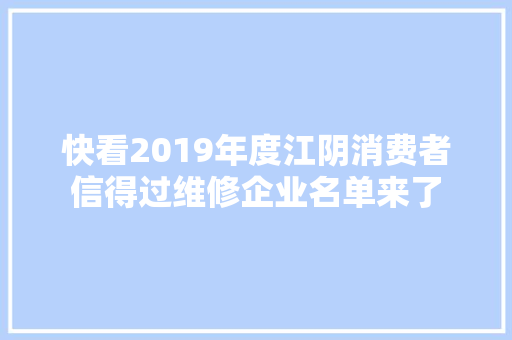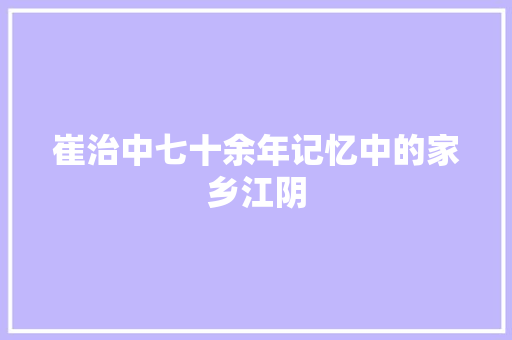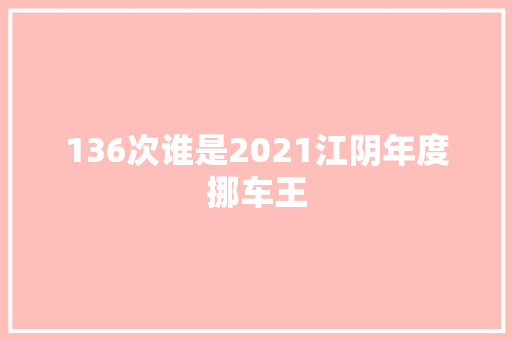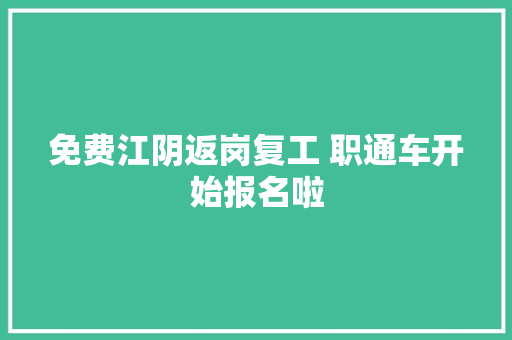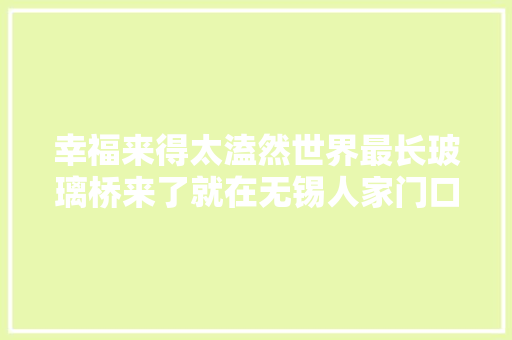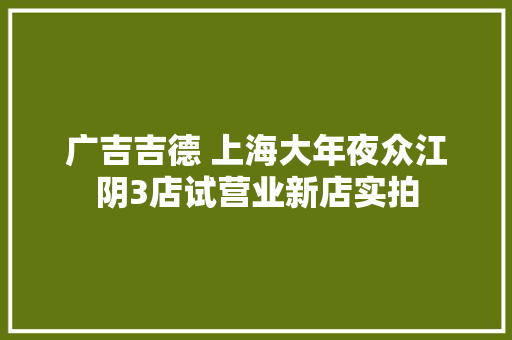作者:沈定荣
此地所说的音乐人并非指专业搞电影、歌曲等方面创作、配器的音乐人,而是特指爱好器乐、爱好唱歌、唱戏的音乐爱好者,权当音乐人吧,当然个中也有专业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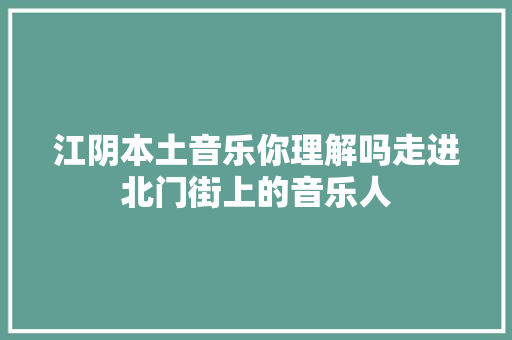
北门街上的音乐人在澄江镇范畴当属压倒一切,芬芳奇葩,这决不是空穴来风,夸夸其谈,其紧张缘故原由是人数多、水平高,且须指出的是在我或兄长辈的这个韶光段。
一年四季,只要你走一趟北门,无论是街上还是河边,便不难会听到悦耳的乐器和歌唱声,尤其是夏天。一到傍晚,人们在家门口泼洒一脸盆净水,搁上门板,摇起蒲扇,谈天说海(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扇)。
正如童谣所道“风凉索索,排门搁搁,老蚕豆剥剥,咸鸭子磕磕”。大热天的,小朋友不再你追我逃,而是乖乖坐在大人阁下猜谜语,念童谣,做游戏。“你姓啥,我姓黄,啥个黄,草头黄……”,“东瓜皮,西瓜皮,丫头家赤骨碌覅脸皮”,“一脉金,二脉银,三脉开始打手心,啪啪啪……”
此场此景中,是谁拉起了欢腾跳跃,似水柔情的二胡,是谁随着歌声低声吟唱?实在真不用问,邮电局对面的张林云、张锦云弟兄俩自小酷爱二胡,慢弓、快弓、抛弓,快速的十六音符,鸟叫、马啸均不在话下。我的印象他们常拉的是独奏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喜送公粮》、《赛马》等。
张林云在利用厂事情,卖力电声乐队;曾在中山公园“爱之梦”舞厅担当键盘手。张锦云当兵回来那年,在镇文化站一曲板胡独奏《瞥见你们格外亲》拉得在场者啧啧夸奖,大林、刘振兴(笛子)和我等均在现场。
张锦云呢在山东济南炮兵部队文工团操琴,当年曾在湖北武汉电台录音《红军哥哥回来了》,扣民气弦,如醉如迷。在江阴县第一届职工音乐会上,他板胡独奏了电影《青松岭》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前》,当演奏第二首曲目《春城节日》即将尾声时,溘然,一根琴弦溘然断裂,小林在独弦高下多次移位,音准到位,顺利完成演出,博得了全场掌声,传为嘉话。
1980年,张锦云在县工人文化宫板胡独奏(相片由锦云供应)
此时,他家门口,又来几个乐友,围成圆圈,来个合奏,歌友们轮番唱唱,其乐无穷,至今不忘。兄弟俩曾在江阴市阳光民乐团中操琴,小林担当二胡首席,直至现在还带学生教拉二胡。同时,曾在红卫厂事情的徐晋才、扬子江船厂事情的许维英,也分别在团中担当大提琴手和二胡手。
原红卫厂的徐晋才在大会堂门前摄(图片由沈勇供应)
他们这班乐友有时也被我哥沈定洪(二胡、小提)叫到我家,在扁豆花爬满了围墙,玉米、茄子、韮菜长得郁葱的院子里,用三根竹杆支起了一只100瓦灯泡,顺风向点起了二包纸盘蚊喷鼻香,开起了音乐会。记得乐友有大林、小林(二胡)、潘仁达(琵琶),陈金才、刘耀洪(二胡),小海(小提)等。
沈定洪在苏州医专时的二胡照(相片由沈勇供应)
我的任务是拿卖棒冰的木块敲打凳子,“啪啪啪”要打在音乐的节奏点子上,当时七八岁,一门心思要出去玩,敲得忽快忽慢,常被责怪,我想:敲这个有啥意思呢?不过,孩提时的音乐熏陶使我终年夜后记忆中的老歌老调还真不少。
此刻,院子迂腐,灯火通明,人头济济,连河西对岸,也不少人伫立不雅观看。我记得他们常合奏的有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和《十送红军》、《乐陶陶》、《彩云追月》等。
沈定洪和个中几个乐友晚上有时还去工人俱乐部(司马街)舞厅伴奏,要买票方进。我拎了一只提琴壳子,才“免检”的。池内男男女女搂搂抱抱,“蓬嚓嚓,蓬嚓嚓”,我没伴玩,没劲,但记的清楚的是乐队中场安歇时,每人有一碗小馄饨,我可吃一半。奏的乐曲只记的是《花儿与少年》三拍子部分。
小林家斜对面是陈金才家,小方桌上的饭菜已撤换上了茶具曲谱;沿河边的高福生等均开始拉起了二胡,以歌曲小调为主。
高福生家住闸桥桥洞旁,桥下自然是纳凉好去处。午觉前夕,他总一人自我陶醉一曲,然后躺椅上一隑,一忽中觉。一次,他拉着拉着,只见庙里阿囡的外孙女(3岁)不当心跌进河里,只能大约摸着看到一双红鞋,丧失落胡琴,跳下水去,在水中一把一捞,捉住小女孩,救上岸后,阿囡对外孙女“啪啪”两记重重屁股,孩“哇”地一声大哭,她竟未说一字,抱起小孩进庙不提……
热爱二胡热爱音乐的76岁的高福生,至本日天仍坚持拉二胡。(照片由福生供应)
高福生,用现在的话评比为“十佳”年夜大好人,名副实在,他救起的溺水者有名有姓的就有12人,胜造84级宝塔。此乃偏题,刹车。
他家有一阁楼。一天,只见几个乐友鬼测测地爬上小楼,我便跟了上去,福生见我没拦(他谈恋爱,我帮他到浮桥营房头传塞纸条的)。干什么呢?哦,原来是偷听唱片(胶木)。我记得是电影《绿色的原野》插曲《草原之夜》和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
啊!
黄色歌曲,不能听!
“阿宝,不能出去说!
”福生关照命令!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邮递员来传情……”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资产阶级情调!
“到处流浪,你看这天下像沙漠,孤苦伶仃,飘流四方……”曲解、贬低社会。
可谁曾知道,《草原之夜》被老外音乐家誉为“东方小夜曲”百唱不厌!
而《拉兹之歌》是著名的天下经典歌曲,至今传唱。走进随便那家卡拉OK厅(或者手机、电脑),输入歌名,急速聆听。李双江、蒋大为、阎维文、郁均剑、刀郎……哪个没唱,而老拉兹80多岁,还现身视屏唱《拉兹之歌》呢。这便是社会背景不同所主宰的!
在兄一辈中,还有我大哥沈定信的小号,曾在杭州公民大会堂2小号重奏《骑兵进行曲》;曾口含2把口琴演奏《拉兹之歌》。他和刘耀明等还常常同台演剧做戏呢,我们百口去江阴公民大会堂看过一次(戏名已忘,内容是抗日捉特务)。我姐沈霞雲会弹凤凰琴,弹、拨、刮均会,并会转调呢。
坛巷弄内五管区排练的锡剧《秋喷鼻香送茶》,沪剧《碧落黄泉》片段。秋喷鼻香丫头誓去世不嫁张家少爷;玉菇临去世苦等志超,影象犹新。陆养德、谢良玉、老阿元等是一次排练都不缺席的积极分子……
说来有趣,邻居阿兴看到我(洗冷浴前聚拢时)便会不经意来上一句“阿宝,我来恭喜侬”(《志超读信》段,把志超改成了我小名),久而之,我也把他的名字换上去:“阿兴,我来恭喜侬”名字是说白,后五字是唱腔,要中低音、深奥深厚、悲切……
夏日的北门街上,被两歪路板一搁,仅存一条夹弄,供人行走。器乐声、唱歌哼戏,似水绵绵;讲老洋话,绕口令,“小热昏”笑声连连。孩提时的影象,似烙印磨灭不去!
只管晚饭仅是一大碗泡饭,萝卜干搭搭……
七八年过去了,我等一代新的音乐人涌现了。
初二时,好说歹说,妈妈给我4角2分买了一枝G调竹笛,便爱不释手,昼夜琢磨,没老师没教材,摸出音阶,吹吹小调而已。文革开始,宣扬队盛行,一有演出,便挤跟在吹笛人后面听,看,进步缓慢。
不过,有一次小飞跃:南京八三师毛泽东思想宣扬队来江阴演出,大会堂济济一堂,好不容易冲涌到乐队后面。吹笛人右手手指在笛孔(小工调)时而逐步移出,时而依次落下关孔,而笛声非常好听。回来几次摹仿一试,也觉好听,效果异样。那别的音孔能否如此呢,如法炮制,很好!
我那高兴劲就不说了。(后来才知是上滑音和下滑音罢)
初三时有同学借我《若何吹笛子》一书,已用白纸包封面,嫡归还,我挑主要部分抄至晚上2点。尚未抄完,只能作罢,同学也是借的呀,无奈。
学校成立了宣扬队,我吹竹笛;澄江桥旁陈希洪在县中宣扬队也吹竹笛(后还拉提琴),我俩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常常合练。夏天,汗如雨下,甚至生痱长疖;冬天三九寒冷,手背冻疮裂尺。
1967年,沈定荣在一中宣扬队时摄,柯尚荣二胡,姚伟澄小提。
花多少力气给多少收成,成正比!
爱因斯坦名言。于是单吐、双吐、三吐、滑音、花舌、历音、喉音均能运用,并能吹上独奏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是一个兵》,《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夏夜,闸桥河边笛声清脆悦耳,悠长奔驰,还能听莅临摹鸟叫、鸡叫、鸟喧、知了叫呢。
宣扬队也常去部队,工厂、各个公社巡回演出。节目无非是唱唱跳跳、歌唱毛主席。例,“语录歌连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惦记恩人毛主席》等。每到一处,尤其是屯子,他们是先接后送,插旗搭台,打鱼割肉,唯恐怠慢了革命小将。有的地方还要忆苦思甜,先吃玉米饼、麦粉粥。
一到晚上,操场上已黑压压一片,水泄不通。文攻武卫战士,手持梭标,四周警卫。在公社干部的呵护下,我们从夹缝中鱼贯而入。“来啰,来啰!
”一片惊喜一片欢呼。他们一吃好晚饭,便带上板凳,周遭几十里,走阡穿陌,早早赶到操场,纳鞋底,做针线,恭候演出。实在,我们是勉强凑合的一台节目,质量并不高,可他们的掌声、欢呼声,他们的激情亲切,我平生未见,大惑不解。
宣扬队中当时的北门人有顾杏秀、魏玉芳、仰书美、夏国贤、沙溶、戴士寅和沈定荣。那时,我17岁开始摸索手风琴(学校的一架32贝司)。
左为作者,右为夏国贤,坐为沙溶(图片由国贤供应)
我除了笛子伴奏外,还有一个节目须上台,三人乐器合奏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和阿尔巴尼亚歌曲《真正的朋友》。从乐器的配备、歌曲选择,演奏的水平均有些低劣,不伦不类。“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全场呼喊,可我们仅会2只。
1968年初,宣扬队终结,下半年,下乡插队。下乡后,我先后参加了村落、公社、市镇宣扬队(笛子、二胡),节目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片断,加上小节目,每次演出我须竹笛独奏一首。
同辈中还有不少音乐人,像港务局的汤振中小提琴拉得特好,常常来张锦云家,向前辈学习,在国庆30周年纪念活动中曾担当首席。
国庆30周年活动结束后,领导、乐队、合唱队在老体育馆合影。(照片由李勇供应)
缪家场上的支边青年管祖荣,其萨克斯的洒脱感和即兴二配,还从事舞厅乐队伴奏也值得称道。福州32105部队归来,住坛巷弄的陈建平在文艺演出队中不但拉二胡,并兼小号、圆号。还有河西吹单簧管的姚斌武,沿河左邻、红卫厂拉二胡的许晋鑫,北大街小学北邻拉小提的高济良,均是同道中人,出类拔萃,常常出没于舞台。
福州部队演出队陈建平(图片由建平供应)
当然,除了“游击队”之外,也有“正规军”。住浮桥头的陈振兴,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张锦云、徐大军都属于专业音乐人才吧。
北门街上的音乐人,其声乐方面也尤为突出。“徐霞客文化旅游节文化展示”、“长江之音”、“1986年开始的家庭大奖赛”、“庆祝祖国出身周年”等等活动中,不少积极骨干一场不缺,诸如红卫厂的李宁花,煤球厂的郑德威,扬子江船厂的沈定荣,亵服厂的郑德源,纺配厂的刘静芬,澄西船厂的缪振琪,还有周丽萍、黄渭勤等均有一副好嗓子。
郑德威和李宁花在老体育馆演出(宁花供应)
徐大军,苏州军分区文工团,男高(江阴中行),《祖国颂》中一段领唱“江南处处有稻米……”其音色幽美,音域宽广,印象难忘。吕国强(北大街小学)一曲《祝酒歌》在江阴通过初复赛,在无锡市赛中得奖。小桥头蒋家媳妇李宁花被誉为江阴的李谷一,每逢江阴大型活动,总之担当领唱,从不降调,现责任在恒大御景小区和蒲桥社区担当唱歌班老师。
左为缪家场上的缪振琪,右为作者(照片由沈勇供应)
1977年,我家院中造了一间七步新屋,便也多次召开音乐会。住北大街小学斜对面老联合诊所内,有一天津航道局事情的老张,每年出海返回可带一大件,那年带回了一台收录两用机(江阴仅广播站有一台)。
巧逢江苏省文工团来江阴演出,便把几首好曲子录回来,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拉着骆驼送军粮》等。那我们起劲了,高济良、徐晋才、陈希洪、陈建平、姚斌武等乐友们便三天两头在我家碰头合奏,听录音记谱,再合奏,提高水平。
在戏曲方面,北门街上更不示弱,先说京剧团吧。北门小桥头北有一蒋家开的兄弟摄影馆(楼上皇后摄影,即结婚照),蒋师母的儿子蒋经国(曾用名蒋经慧,后又改为赵凯),须生,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演少剑波,其父母、姊妹懋櫟、老虎、阿德、阿咪我均熟习。
大弄口小菜场宰肉的何顺福的儿子何建华,武生,其武功了得,在《智取威虎山》中饰杨子荣,他弟弟均华和我同学,几个娘舅也和他父是同行。近后街的杨宗平,小生后转须生,《沙家浜》中饰刁德一。还有花脸张小毛,颇有名气(有船,常泊北门)。
这些角儿,我印象最深,敬佩致之,大家一定熟习吧!
还有青衣刘静仙、徐瑞竹、周玲珍、刘秀娣……1960年吧,县小京班就在君山武庙——关帝庙大厅排戏、练功、吊嗓。
据地区京剧团,刁德一扮演者,江阴电视台专栏“山海经”主持人朱永继先容,苏州地区地委布告、军分区司令刘金山(《铁道游击队》刘洪原型)喜好京剧,八个县中竟无一个象样的剧团,即抽调江阴团14人充足地区京剧团。那抽了14个骨干,剩下的还象京剧团吗?不去,要么全去!
于是,1969年,包括炊事后勤全体人马一起转入苏州地区京剧团。
京剧团部分人于中山公园合影(图片由秀娣供应)
1960年2月在南街还成立江阴县戏曲学校,有京剧、锡剧和歌舞三个班。
戏校校徽(秀娣供应)
蒋经慧、何建华、杨宗平、张小毛、刘秀娣、刘静仙、陈和平等均是小京班的北门人,本色上便是江阴县京剧团的前身,而1969年江阴京剧团转入地区后,江阴便没有京剧团了,咋办?于是1971年便再次成立了小京班,但好景不长,不久便转团的转团,进厂的进厂,例陆宝华,唐炳泉、顾美娣等。
左为陈和平,刀马;右为刘秀娣,青衣。(图片由秀娣供应)
浮桥冷冻厂东隔壁包家大院是我外婆家,而西邻一家老宅子是“锡剧王子”周东亮家,如今是江苏省锡剧团团长。他打小就随锡剧团的父亲周林华,在浮桥河边吊嗓练功,多年磨炼,终成名角。他嗓音清亮,声情并茂,字正腔圆,《玉蜻蜓》、《珍珠塔》、《白蛇前传》等均是他拿手剧目。2020年9月3日,周团一篇《夏日记趣》(可点击阅读),详尽先容孩提时景况。
周东亮童年时的锡剧演出旧照
我隔壁的李国强常跟娘舅刘耀明刘耀洪练唱锡剧,当年也考进了大丰锡剧团。而其他剧团我熟习的张佐一、陈(王权)、沈君义、冯仲祖、姜福龙、杨祖良、许老师、缪玉华、陈建国、徐金芳老师们,后来也常常参加庆贺活动,开琴行,传授教化生、做主持等,此乃旁话,插上一笔。
至于业余的爱好者也泛泛其多。老年大学、老年宫、城中社区、芙蓉社区便是票友们聚唱之地,现国标舞蹈协会的刘福澄每周要去4次为票友们伴奏戏曲。1991年江阴市总工会举办的徐霞客文化旅游节京剧卡拉OK赛中,小桥头的唐秀萍《光辉照儿永向前》得到二等奖。河西的陈金成自幼好京剧,古稀之年,《沙家浜》中《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如今竟原调演唱,有板有眼,音域宽广。
作者一家在比赛中《铃儿响叮当》、《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故然,这些票友们年事偏大些,演唱曲目年轻人大多数不喜好,但这便是忆旧,这便是文化,这便是传承。
九十年代,泰西的铜管乐器开始在江阴盛行(实在也有木管、打击乐器在内)。兴澄钢厂打响了第一炮,继而,钢丝绳厂、铁合金厂等相继成立,扬子江船厂是1991年4月成立的,这样北门就有三支:钢丝绳厂、澄西船厂、扬子江船厂。往后每逢喜事例市委市政府表彰大会(连续请我乐队9年),像开业签约、大船竣工下水出厂、各州里的喜庆等均叫上铜管乐队热闹一番。但长江大桥奠基、文化旅游节、国庆升旗仪式等重大仪式均是百人铜管乐队,且边奏边行进,李勇老师担当总指挥。
扬子江船厂管乐团合唱队参加市总工会举办的《五月歌会》(沈勇摄)
后来,市文化馆倪萍又成立了礼仪队,浓妆艳抹,高叉旗袍,漂俊秀亮的姑娘们服式整洁、鲜花、剪刀、托盘、彩球……“鸣炮!
”“奏乐!
”于是,黄磊作曲的《江阴市市歌》作为开头曲。队员们制服着装,铜管乐无须扩音,洪亮宽广,的确气势。
稍统计了一下,十几年来,我担当指挥的演出有300余场,不包括李勇校长和其他单位临抽的演出。约2003年,铜管乐队渐至淡宠,仅剩个别爱好者在开琴行,传授教化生,自娱自乐,也有个别队员参加了“白事”军队。李校长还组织十名妙手去“三毛”、“职大”、“南菁中学”、“山不雅观中学”等单位去担当教员,成立新乐队。
铜管乐队在江阴船厂改名为江苏扬子江船厂仪式上迎宾(沈勇供应)
进工厂30多年,我没有放弃音乐方面的爱好,并兼学习拍照、文学、书法等,以提高自己的审都雅及综合水平。
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的李勇老师带我去各单位伴奏,排练节目。刚开始是“随着大人吃喜酒”,除了伴奏一样不管。他是科班出身,音乐综合知识丰富,我向他学到了好多东西。例华联公司、证券公司、技改局、公安局等单位的大合唱,小合唱。
我边伴奏边听边琢磨,一贯到自己能单独进行编导排练,例澄西船厂、糖果厂、五一棉纺厂、纺织机器厂、劳动局、交通局等,能单独指挥,并多次担当过市、局卡拉OK赛的评委,也得到过市级歌曲创作的二等奖、三等奖。
作者指挥百人大合唱
退休啰,北门人的音乐人没有退!
他们跳起了广场舞,走进了卡拉OK厅,挤身于元林老年大学,阳光女子乐坊,参加了天华合唱队,老年合唱队……以幽美高亢的旋律演奏歌唱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公民以及美好的生活。
作者寄语
随着城市范围迅速扩大,布衣百姓不断燕徙新居,电话、信息均难以索求,故采访不到位,情形不全能核实。
所谓往事,均属陈年往事。早,60年之前,晚,退休之后,仅凭影象,会有不敷之处,例姓名中别字,不知大名仅知小名,韶光有时交待不清,此乃其二。
其三,“音乐人”即指我熟习的朋友邻居,但也会有遗漏。例北门(城墙)北面有利用纱厂女工宿舍,宿舍西面便是老校长陈荣卿家,其令郎陈昌、陈楠、陈畊好几个便是器乐爱好者。况且还有我不熟习的北门人呢。
故凡不敷之处,望多见谅。
来源:乡愁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