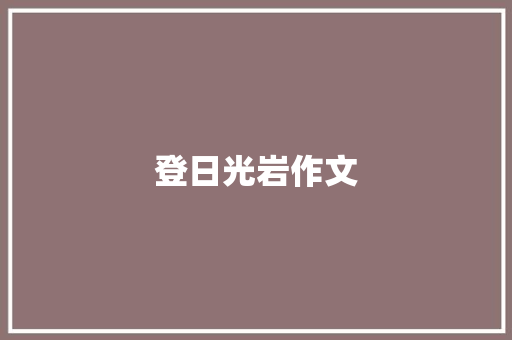作者:宋瑾(福州大学讲座教授,中心音乐学院教授)
厦门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多见白鹭翩翩飞行,故称鹭岛。鹭岛之外有个“卫星岛”叫鼓浪屿,与金门隔海相望。近40年来,一首《鼓浪屿之波》传唱海内外。那微波起伏的曲调深情动人,诗意浓郁的歌词拨动多少思乡者的心弦,更唱出祈盼祖国统一的两岸公民心声。

“思乡水煽惑波浪”
据记载,鼓浪屿呈椭圆形,四周遍布沙滩,故初名为“圆沙洲”。该岛西南角海边有两块交叠的岩石,在海水侵蚀下涌现一洞,每逢潮涨潮涌,浪拍岩石,发出擂鼓之声,便有了“鼓浪石”之名。明朝始将圆沙洲改为鼓浪屿。鼓浪屿最高处这天光岩,原名“晃岩”。明末为了收复被荷兰侵略的台湾,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设水操台,演习水师。他登高眺望,赞其景致赛过日本的日光山(另一说为吉林图们的日光山),便将“晃”字拆为二字,于是有了“日光岩”之称。鼓浪屿因郑成功的历史功绩而名扬四海,成为一个独特的“英雄”与“思乡”领悟的民族文化地理符号。
1981年12月,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福建省委对台办、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开国平易近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等联合组织音乐采风创作活动。福建省内外14位词曲作家到平潭、晋江、惠安崇武、厦门等地体验福建沿海区域地方文化,创作了百余首台湾题材的歌曲。曲作者钟立民,词作者张藜、张红曙也参加了这次采风。在鼓浪屿,词曲作者3人共同登上日光岩,获取直接感想熏染,在各自的灵感涌动之中创作了《鼓浪屿之波》。
钟立民是江西南昌人,对台湾民歌民谣情有独钟,爱听鹭岛群众诉说台湾亲人的故事,也爱听《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亲自感想熏染海峡两岸特有的闽南音乐风采,为歌曲创作奠定了主要的根本。
这一年,55岁的钟立民第三次来到厦门。住在鼓浪屿的日子里,他听着浪花拍打沙滩礁石的声音,波涛般的旋律油然而生。除了《鼓浪屿之波》之外,他还创作了同类题材的作品《我爱鼓浪屿》《鼓浪屿之恋》《啊,鼓浪屿》《集美学村落的灯火》《厦门为什么这样美》《凤凰花开》等。
张藜是辽宁大连人,《竹篱墙的影子》《亚洲雄风》《我和我的祖国》《山不转水转》等都是他作词的歌曲。当年,他为钟立民的曲调填词,也是从鼓浪屿的波涛声中得到灵感。当时他跟一位室友同屋而眠,夜里被室友的鼾声影响得难以入眠。自然界海浪拍击声与人类的鼾声形成奇异的交响,更有钟立民幽美曲调的诱发,加上白天日光岩的登高眺望的体验,造诣了《鼓浪屿之波》的诗意词句。
张藜创设了一个台胞登上日光岩纵目海峡东岸,思恋家乡的情境。“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通过写景进而抒怀,“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俏丽的基隆港。”词曲结合形成了盼团圆、盼统一的完全作品;它就像满载亲情的航船,很快就驶入海峡两岸千万同胞的内心深处。
张红曙是原济南军区艺术辅导委员会委员,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艺术辅导。他对张藜初填的《鼓浪屿之波》歌词提出一些改进见地被采纳,遂成互助填词的作者之一。
这3位词曲作家都不是厦门人,却能写出闽熏风度浓厚的动听歌曲,由于他们和祖国大江南北的人们一样,具有祈盼台湾回归的共同心愿。
从“和弦外音”到吉尼斯记录
那次采风,厦门歌手鲁帆卖力接待第一次见面的钟立民等词曲作家,带他们逛鼓浪屿,爬日光岩,也为采风团搜集台湾歌曲。次年,鲁帆收到钟立民的一封信,附带一页歌谱。作曲家请他试唱《鼓浪屿之波》并提见地。
1982年1月20日,在北京举办“海峡之声音乐会——献给台湾同胞的歌”,李光羲首唱《鼓浪屿之波》。据厦门词家朱家麒回顾,钟立民曾对他说,李光羲在演唱的时候,有听众说“难听”。可见当时还有人不习气改革开放初期从刚硬乐风向柔美曲韵转变的审美意见意义。当然这仅仅是微弱的“和弦外音”。这首心随波涌的歌曲很快就广为流传。
1983年,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演唱《鼓浪屿之波》,歌曲获国家新歌评比精良作品奖。
1984年,张暴默在央视春晚演唱,立时产生广泛影响。
1987年,女高音殷秀梅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鼓浪屿之波》。
1988年,歌曲获厦门市政府颁发的首届文学奖特殊名誉奖。
1991年,殷秀梅在中心公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节目中演唱,再次向海峡东岸送去深深的情意。
1998年9月,《鼓浪屿之波》乐谱被镌刻在厦门国际马拉松赛道环岛路上,成为独特的音乐雕塑。它有247.59米长,被列入吉尼斯天下之最。
《鼓浪屿之波》频繁涌如今厦门航空公司的航班,被用于厦门海关的钟楼报时,以及当地各种节庆、仪式等活动中。它被改编为合唱、钢琴曲等,还涌现京剧版等新形式,在祖国各地传播。多少人被它吸引而来到厦门,来到鼓浪屿,站在日光岩眺望海峡对岸。这首歌唱出两岸公民统一祖国的共同心声,也给厦门带来各种物质与精神的互换。
“逆向抒写”与“正向抒怀”
不少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剖析过《鼓浪屿之波》的词曲特点,阐释过歌曲的意义。从浩瀚评论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见地都充分肯定歌曲的艺术代价、人文代价和时期意义。再现性单二部曲式构造的旋律幽美动听,海峡音韵浓郁,这一点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但也有一些同行认为这首歌曲的歌词采取的是“逆向抒写”,即台胞在鼓浪屿抒发对家乡台湾的思恋之情,而不是大陆同胞呼唤台湾回归祖国的热盼心声,在祖国统一的主题领域还有提升的空间。
于是涌现了多少重新填词的事例。这些新词都是“正向抒写”,有的新词还得到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但是,不附和新词的同行指出,新词存在措辞音调与旋律腔调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一首歌是否被社会接管并传唱,关键在于广大受众的认同。从实际情形看,《鼓浪屿之波》的原作还是深受广大公民群众喜好,并在几代人中原样流传。从学理上看,歌词原作的抒写角度跟作者填词时的境遇和身心状态密切干系。词作者作为外村落夫来到鼓浪屿,站在日光岩上,很自然地以“人在异域为异客”为角度来构思歌词内容;日光岩上鸟瞰海岛美景,显然又乐于融入当地,乐于以异域为家乡。夜里听涛起意,便造诣了“逆向书写”办法的“正向抒怀”。台胞从台湾来到大陆,已经绑定了一根由海东到海西的绳索;在大陆思乡,又绑定一根由海西到海东的绳索。这两根绳索就像结实的纤绳,将大陆和台湾牢牢拉在一起。这使表面柔美的《鼓浪屿之波》具有内在的张力。
台湾和大陆分离了70年,《鼓浪屿之波》歌唱了近40年。本日,这首歌在新时期中得到新意义。它将连续唱出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两岸公民祈盼团圆的心声随着波涛一起脉动,深奥深厚而又有力。
鼓浪屿之波,亲情之波。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0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