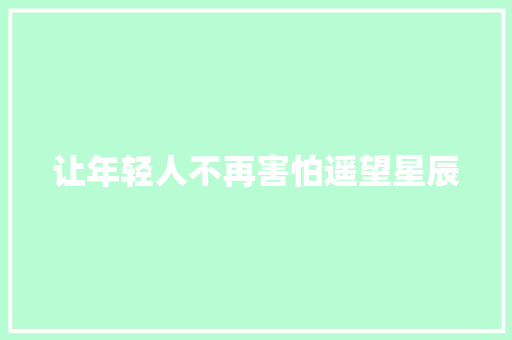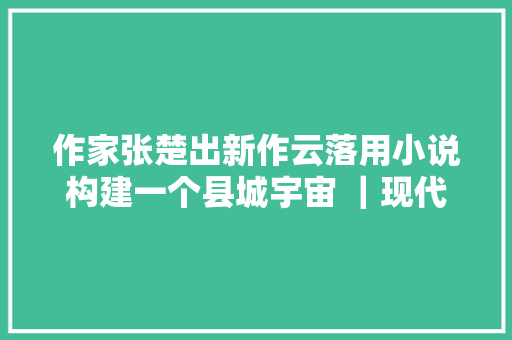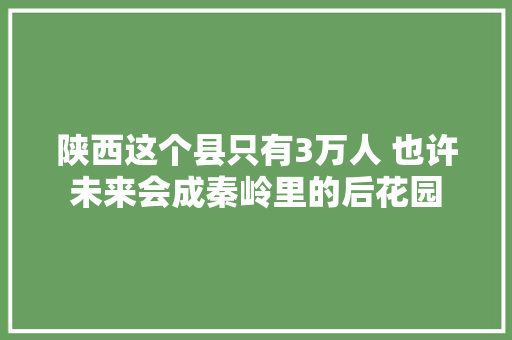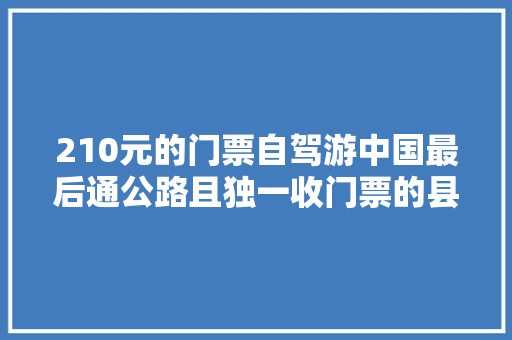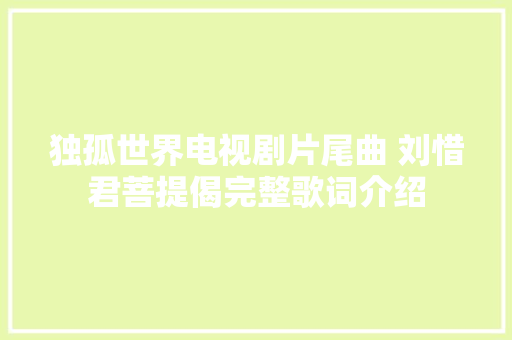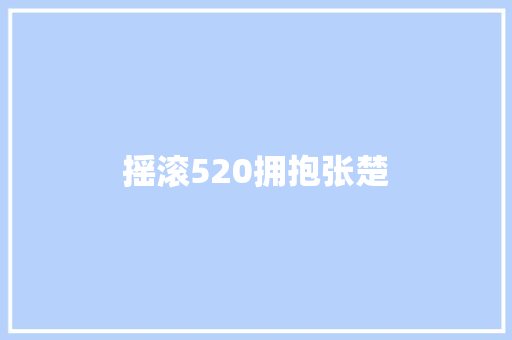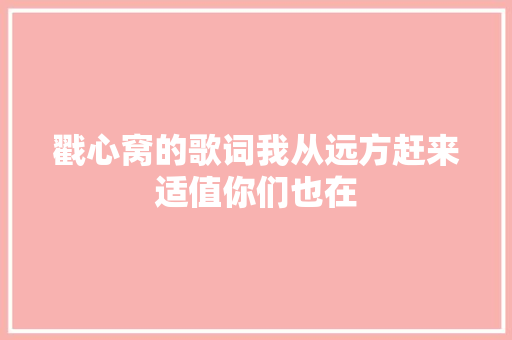这个专题能够做出来,是从孙频中断自己手上的一个中篇小说,支持我一个短篇开始的。然后,有了“在县城”这个核心词;然后,立时想到张楚和阿乙的那些小说的县城。关于张楚,虽然他后来写了许多更好的小说,但我一贯难以忘怀的还是他2003年的《曲别针》。冷冽。读阿乙则是从他的《灰故事》,该当是上海三联的那一版吧?孙频的县城是山西交城,她在县城18年,直到去兰州大学读书。阿乙的县城是江西瑞昌。据他自己说,他的离开是逃出小公务员无望的生活。张楚一贯生活在河北的滦南。去年夏天去北戴河,高铁停唐山,我知道离张楚不远,下车拍了一张站台的照片发给张楚。
张楚现在已经被天津作协作为人才引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常住滦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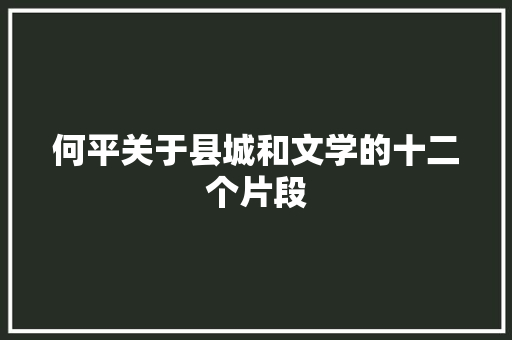
02
操持中的这个专题由小说家的虚构文本和我对他们的县城拜访记组成。平时只在他们的小说里读到他们的县城,我想去实地看看。朱燕玲主编竟然对这个拜访也有兴趣。我们立时分头和他们确定拜访的韶光。记得那天是元月十四日,南京评论家协会换届,以是能够记得确切韶光。张楚一贯在滦南。孙频会回交城过年。阿乙去四川的夫人老家过春节。故意思的是,去到这三个县城,都要先抵达它们最近的中央城市武汉、太原和唐山。在中国,交通不但是交通问题,交通每每决定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的区位和层次。
按照操持,我年前先去瑞昌,韶光定在我回老家之后。元月十九日,我从老家回到南京。二十三日,武汉封城。经由武汉去瑞昌的操持落空。继而,疫环境势严重。禁足而不能出行。
因而,这个专题该当包括一篇未完成的拜访记。
03
关于县城和全体中国的关系,我微信问询过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村落庄社会研究的邹农俭教授。邹教授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费孝通师长西席苏南村落庄课题的研究,选录他的微信如下:
中国的县在中国历史上特殊故意义,它是中国行政建制资格最老的,从秦始皇郡县制开始,很多建制府州地区早已消逝,唯独县历时两千多年至今仍是非常主要的一级建制。文学家洞察到了历史的深邃,于是有了很多文学作品,只是在当代化城市化的大潮中,县逐步不吃喷鼻香了,开始衰落了,特殊是我们的系统编制设定,将县作为村落庄传统来对待,同样是正处级,县长与市长不一样,这是很可悲的。
社会学是研究现时期那些热门的东西,社会上什么时髦什么热门就去追什么,以是很少有经典留下来,充其量是些所谓经世致用的东西。我以为文学家对此关注深刻,特殊是那些写村落庄的作家,描写村落庄一定有县城。尤其是这次疫情,要好好琢磨琢磨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度崇尚大都邑,还要搞什么城市带,看看武汉这个大都邑,疫情为什么发生在这里?为何那么久扼不下去?
确实如邹教授所说,文学的县城很多,比如最有名的可能是路遥的《人生》——到县城去,曾经是多少村落庄青年的中国梦。邹教授影象的文学,大概是二十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时至今日,文学的县城也在越来越少。
04
我的县城影象和海安、如皋干系。它们间隔我出生的村落庄都是十几里。初三之前在村落小学念书。村落小孤零零地在成片的庄稼地中间。初三到乡里读。这个叫丁家所的小镇,该当曾经比较主要,我在东京大学藤井省三研究室无意看到一本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舆图集。海安一共有四个地名被标注出来,丁家所是个中之一。但撤乡并镇之后,丁家所这个小镇的行政功能已经变得微弱。丁家所,就有一条老街,有些老店铺,像民国旧电影里的样子。两年前,我们回去看,已经败落成不成样子。
村落庄少年,不看到县城之大,就不睬解州里的小。而由于有了州里的小,县城便是大的城。在县城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城里人。高加林是这么理解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以是,阿乙的《遇见未婚妻》,父亲要到县城买房,带领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进城;张楚的《和解云锦一起的多少瞬间》,辍学的解云锦进城打工。
海安和如皋的县城,在前者读了三年的高中;在后者事情了十年。记得第一次去海安,是乘船从串场河进去的。串场河在海安出去的墨客小海的诗歌里写到过。小海有首著名的诗歌《北凌河》。在海安,串场河和北凌河是齐名的。三年,熟习了县城网状街巷编织的地景:新华书店、医院、学校、澡堂子、饭铺、百货公司、理发店、县政府、能买到文学杂志的邮局、放电影的戏院、工人文化馆和放录像、打桌球、舞蹈的文化馆等等,工厂和车站在城的最边缘,像孙频的《猫将军》,最荒漠和混乱的地方也在城的边缘。也是这三年,写诗折腾文学社,堪堪摸着文学的边。至为忧伤的是,少年时期膜拜的县城墨客和小说家末了也都止步于县城。实在,可以做一个野外调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县城有过多少文学青年?
第一次去如皋,是在去海安县城读书之前。我和一帮顽劣的小伙伴纵火烧了生产队的草垛。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为非作歹。不知出于何故,外婆反而骑车带着我去了心神往而不达的如皋县城。影象中,我们是从北门穿过石板巷子。少年的觉得是如皋是一座繁华落败的大城老城。也确乎如此,如皋和海安比较起来,有更古老的寺庙和园林。
县城便是县城,不是村落庄,也不是一样平常的小镇。如皋早便是县级市。海安,去年也是县级市了。
确实,该当一贯到新世纪前后,县城一贯为中国文学运送着文学青年。他们里面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大多数还剩余在县城。这是那个时期文学繁荣的基座,纵然他们不能成为一个精良的写作者,至少是一个精良的读者,他们是县城的小职员、西席、工人,等等。
但是,时期的变革是剧烈的。我检索了下《中华文学选刊》去年对117位“85后”作家的问卷调查,创造在县城写作的微乎其微,乃至从县城出发的写作者也很少见。但另一方面,据我所知,在县城写商业网文的还有不少。无论如何,写所谓严明文学的文学青年撤出县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大概能部分阐明当下村落庄文学不振的现实。
05
关于县城,不但是文学的私属领地。“五条人”《县城记》的海丰包括:《十年流水东十年流水西》《倒港纸》《乐乐哭哭》《踏架脚车牵条猪》(骑辆单车牵头猪)《问题涌现我再见告大家》《绿苍苍》《梦想化工厂》《道山靓仔》《李阿伯》《童年往事》《阿炳耀》,个中《踏架脚车牵条猪》唱道:
唉,朋友 /你莫问我 /有没搭过海丰的公共汽车 /我常常看到它,载着空气/从“联安路口”至“云岭”
唉,朋友 /你莫问我 /有没听过,海丰汽车、摩托车的噪声 /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怕了
我踏架脚车牵条猪 /(站在东门头,暴力撒泡尿,买辆拖沓机) /我踏架脚车牵条猪 /(龙津溪是一条河.三十年前已经残废了) /我踏架脚车牵条猪 /(屯子不像屯子.城市不像城市.海丰公园只建一个门) /我踏架脚车牵条猪 /(小的时候我跟阿公讨两毛钱,他说你拿把铁锤和口盅来,我敲鼻血给你得了)
另一首《十年流水东十年流水西》:
他们都说我是在说梦话 /实在我说的还是海丰话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啦啦啦啦/本日环球化.嫡耍自我
“五条人”说他们是“立足天下,放眼海丰”。《县城记》获颁《南方周末》2019年度音乐,他们的感言是:
《县城记》是一张讲故事的唱片——“倒港币”的故事,农人“李阿伯”的故事,单身佬“阿炳耀”的故事,“梦想化工厂”门卫的故事……这些故事,平常得就像“平常”两个字,这些平常的故事,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藏有许多,而每一期的《南方周末》,藏的都是这样有故事的人。那么好吧,我们把《南方周末》的这份“特殊致敬”理解成:不是颁给《县城记》这张专辑,而是指向活在大城市、小县城里的每一个平常人。希望我们这样说,不至于让人觉得到矫情。……《县城记》还是一张用你们的“外语”唱歌的唱片。
06
贾樟柯可能是最多以县城为背景的中国导演,他的《小山回家》(1994)、《小武》(1998)、《站台》(2000)、《任逍遥》(2002)、《山河故人》(2015)都发生在县城汾阳。贾樟柯说:
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足的韶光去感想熏染生活的乐趣。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店铺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卖菜的卖豆腐的卖书报的,银行里头的职员,对面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你都认识。中午吃晚饭睡个午觉,一贯睡到自然醒,三四点骑个自行车去某个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吃晚饭打麻将,一贯到筋疲力尽睡觉。这种生活是有美感的,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殊舒畅。但是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地皮,还是相称呆板。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我对贾樟柯灰扑扑的县城最有觉得。汾阳离孙频的交城该当很近。离我家乡的县城很远。但那无所事事的街角少年和桌球台,和我影象中八十年代末的县城险些一样。乃至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也看到这样的小镇和少年。实在,有很多地方离得很远却靠得很近。
07 许知远和阿乙的访谈有一段关于阿乙的县城。
《单读》:这些年你也不断地回家,看到县城的变革是什么样的觉得?
阿乙:县城现在从物质上来说,频年夜城市乃至要好。它只有几个指标不太好:一是煤气,可能还在用煤气罐,这是我比较讨厌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采暖,像在南方,采暖不像北方这么方便。但剩下的生活条件切实其实太好了:一是巨大的空间,你在北京住50平方米,在那儿200平方米都能搞得下来;还有一个是美好的景象。但我现在仍旧恐怖回到县城。前两年常常做噩梦,梦见我父亲拿着一个蛇皮袋,和家人一起又把我抓回去了,塞在某个单位上班。前些日子,有人建议我回老家,在当地文化部门上个班,帮忙做推介,由于我现在写作有点名声。当时也没谢绝,后来以为这个事情挺荒谬的,真要去了,心里肯定很悲惨。
而且我离开县城有一个巨大的缘故原由,便是我在那儿买不到什么书。买书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报亭,报亭更新比较快,能买到的好东西便是《杂文选刊》《读者》《涉世之初》这样的杂志;二是新华书店,但也买不到文学书。我现在想,为什么县城的人比较喜好看《环球时报》?为什么杂文在县城知识分子里比较盛行?柏杨、李敖、王小波他们写的东西固然很有先见,但好多年重复讲一个问题,结束在某一个地方。我如果要获取更多的东西,在县城里肯定弗成。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知识分子,写了很好的文章,办了很好的杂志,写了很好的书,但他们的东西进不了县城。这种情形下,实在只有离开。后来到北京,才能打仗到这些多元化的东西。假如在县城,你的精神生活不得不被凤凰传奇、汪峰所决定。我QQ、微信群里的高中同学,包括当时我认为思想上比我前辈多了的人,现在跟他们谈天,非常诧异,他们转发的,每天咋咋呼呼,吓去世人。人的意识实在是被县城的大众文化吞噬掉了。
和县城扞格难入的文艺青年,那些精神的流亡者。
08
同时期作家中,以张楚的写作成绩和有名度,和县城纠缠得这么深,依然在县城安家的,可能绝无仅有了。他有两篇常常被人引用的笔墨,一篇是《在县城》:
1983年从大同迁徙到这个叫作“倴城”的县城,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除了在大连上大学的几年,除了有时的公差私差,我一贯不舍昼夜地住在这里。
县城发生变革是近十年的事。之以是变革,是由于这里开了几家私营钢厂。每个钢厂都很大,都有很多工人,闹哄哄的,热腾腾的,空气里的粉煤灰落在他们脸上,让他们的神色显得既骄傲又落寞。逐步地高楼越来越多,而且前年,县城终于涌现了超过20层的高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我们这里还常常地震,人们都怕住高楼。而现在,人们彷佛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不怕了,有了点钱还专门买好车。我很多小时候的同学,现在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公司的董事,坐在几百多万的车里朝你亲切地打呼唤。就像《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一样,这个县城越来越光怪陆离越来越饕餮好食,空气中的味道也发生了质的变革:以前虽灰扑扑、干燥,但骨子里却有种干净的单调和通亮,我相信那不是景象的缘由,而是民气的缘由。如今,小镇上虽有了肯德基,有了各样专卖店,有了各种轿车,可人却越来越物质化和机器化,谈起话来,每个成年人的口头都离不开屋子、金钱、女人和权力,彷佛只有评论辩论这些,才能让他们的身上的光芒更亮些。
我想,或许不单单是这个县城如此,中国的每个县城都如此吧?这个步履匆忙、满面红光的县城,无非是当下中国最普通也最具有范例性的县城。在这样的县城里,每个月都会涌现一些新鲜事,当然,所谓新鲜事,总是和偷情、鸩杀、政治阴谋、腐败连接在一起,归结到底,是和俗世的希望连接在一起。可是由于这种希望如此堂堂皇皇又如此司空见惯,我总是忍不住去关注一下,于是,我创造了很多有趣而悲哀的故事。
县城是熟人社会,熟可能更多是表象,相见不相识是实质。就看这个专题的三个小说,每一个县城故事都有独属的幽暗秘密,乃至是致命的秘密。以是,县城的文学动力可能不但是独异的空间和区位,而是社会样本和人性。
网上流传着张楚其余一篇关于县城文艺青年的更有名的笔墨是《野草在歌唱——县城里的写作者》,这篇笔墨首发2014年第12期的《文学港》,后来收入他的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
1999年的倴城像个哀伤简约的符号——它是所有北方县城的缩影。从1984年我们搬到这里,多年内它没有显著变革:波折狭窄的主街每到放工时就堵车,而主街两旁是低矮破旧的门市:开理发馆的温州人、开川菜馆的成都人、卖板鸭的南京人、开性病门诊的广州人、售熟食的东北人……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将门脸洞开,让平铺直叙的阳光打进,在他们或清爽或油腻的脸上投下或通亮或黯淡的影。在年复一年的买卖中,他们的腰佝偻了,皮肤泛着哀伤的牙黄色,指甲缝熏染着小城独占的气味:纸糨糊味、钢厂的粉尘味、从迢遥海边传来的水底动物的腥味。有时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倴城,看着众生万象,噜苏的幸福感会丰裕满我的内心。我知道,早晚我会写出他们的心灵史。犹如上帝造人。
这是县城文艺青年的挽歌。类似顾长卫的《立春》。《立春》在建制上可能是比县城大的小城。但也是县城故事。有时候,县城故事可能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确切县城。以是,把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及美学意义的小镇青年写作都放在一起,大概都是可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县城故事是献给那些城乡灰色地带的。
09
在百度上同时输入“孙频”和“县城”,会显示出她的许多小说。是的,在早期写作里,县城是她小说人物要逃离的地方;而到了晚近,县城每每是逃离者溃败的归处。这中间的变革不但是一种情节的翻转,而是心境和审美意义的。她说过:
去年(摘录者注:2018年)我回到老家的小县城过中秋,闲来无事,一个人在老街上溜达。老街上有半截千年石狮子,风化不堪,它陪伴了我全体童年和少女期间,读中学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它身边掠过,未曾多看它一眼。可是那天,我在深秋金色的阳光里久久看着它,想起了过往那些剔透晶莹的光阴,懵懂无知,充满抱负,忽然就觉出了到底什么是沧海桑田,什么是岁月。我忽然就从它身上感到了一种奇异的东西,一种类似于慈悲或恩典的东西,重重击打着我。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很普通,却险些让我落下泪来。从前我害怕扎进人堆,恐怕自己变得噜苏而平庸,从不肯轻易体谅与宽恕自己的差错。可那个下午,我在最普通的人身上忽然看到了最残酷的一壁,不是鲁迅那种对国民性的批驳,不是伪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俯视,也绝不是虚无的怜悯与哀叹,真的就只是看到了每一个个体身上奇异的生命力,薄弱、残酷、多姿,深陷泥塘又几欲飞行。小说的题目便是在那一瞬间涌现的:狮子的恩典。对众生的恩典。亦是对自己的一种恩典与赦免。是的,这么多年里我常有无力感与嫌恶感,时常无法体谅一个平庸与感性的自己,可是我究竟还算是一个努力的人。
孙频的县城在她发给我的照片上看过,荒疏和颓败。这样的地方能够成为归乡吗?
10
远子在豆瓣成名。2019年,他的《白日漫游》入围了宝珀空想国文学奖。同年,辞去北京的事情,离开熟习的文学圈子,回到家乡湖北红安的县城和屯子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里连续写作。(《远子的2019:北漂十年出了三本书,32岁回到县城》,“GQ宣布”微信公号)
远子是本专题邀约的作者之一。他的县城红安疫情严重,以至于无法完成构想好的小说。谁此时此刻在此地能够从容地写作?
此前,广东小说家陈再见,彷佛也回县城,写县城系列小说了。
11
小说家黄孝阳去年的《人间值得》写了一个县城无赖的简史。更早一些,付秀莹的《他乡》,县城也是主人公翟小梨生命远行的一站。70后作家许多都是从写州里开始,这也是他们的原生履历。这些原生履历并没有枯竭。他们也远远没有产生跟原生履历匹配的伟大作品。
以地标为中央不雅观察作家和作家的关系,现在已经不常用。也不尽然,比如最近两年铁西区就成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地标。从铁西区放大到东北,做新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学”,是大众传媒和大学正在努力的事情。能不能做成?做成了,这个筐可以装进去什么东西?尚属未知。
但县城不一样。不同的县城,有时候却共有同样的文学底色,比如张楚、阿乙和孙频小说的灰色和绝望。或者说,所有的中国县城,它的描述、肌理、腔调和骨子里的气质,是兄弟姐妹一样的。
“县城”(可能还应包括市郊和内地比县城更大的小城)作为一个文学空间,一个文学的“地方”,既不是乡土写作,也不是城市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把稳力更多在城和乡两个极点上,除了这两个极点可能还隐伏着第三种文学传统谱系。我也就县城问题咨询做人类学的淡豹,她给我整理了近万字的材料,供应了许多各学科有代价的不雅观点。从社会学的路径进入,淡豹认为:
“县城有可能代表着‘内地’(middle countries)、‘腹地’、文化守旧主义、执拗、闭塞等文化特点。对付一个屯子青年,县城可能并不代表着‘城市化的第一步’,而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它的诸种文化特点,和心目中进步的城市是截然相反的,又没有村落庄的自然。县城大概不是城乡之间(乡城之间)的停泊站,而是另一种迥异于北京、上海的知识/政治精英想象下的中国的样貌。这样看,如何把地理空间理解为文化空间,就并不是一条村落庄—县城—城市的标准、线性、进步叙事。”
比如淡豹也提到的师陀的《果园城记》。师陀小说写:“这个城叫‘果园城’,一个假想敌中亚细亚小城的名字,统统这种小城的代表。”不但是《果园城记》,民国新文学里有大量的写知识青年救世和启蒙的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和“地方”该当都是“县城”(小城),这些小城也确实是“内地”(middle countries)、‘腹地’、文化守旧主义、执拗、闭塞的,但改革开放以来,“县城”的文化构成变得繁芜,比如改革文学里,县城既是守旧的,又是激进的。
12
张楚的《和解云锦一起的多少瞬间》、阿乙的《遇见未婚妻》和孙频的《猫将军》放在一起看,能够看到中国城乡地理。下乡,到顾家庄、今一乡,县城是一座城;到北京、郑州和杭州去,县城又被无数的乡拱拥着。这是中国县城的空间现实——“乱”,也可以说是发达着活力。而县城的韶光,在他们小说对应着小人物的成长史。各自的县城都生活着自己的亲人,面对自己和亲人的县城,小说家自然会收敛起高高在上慈善主义的优胜感和同情心,而代以老实的人性主义的共同命运感。这是他们小说的动人之处。
来源:《花城》2020年第3期
微信编辑:刘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