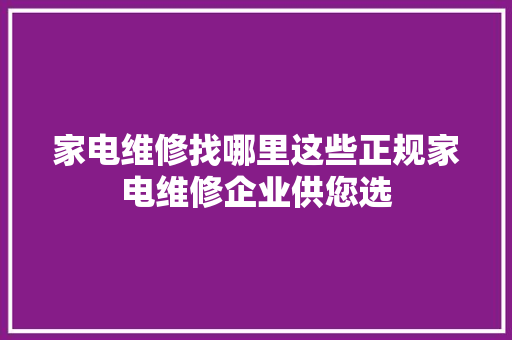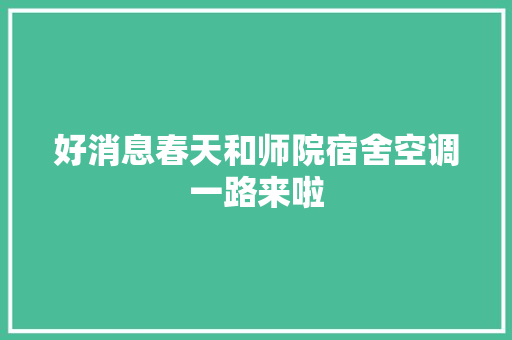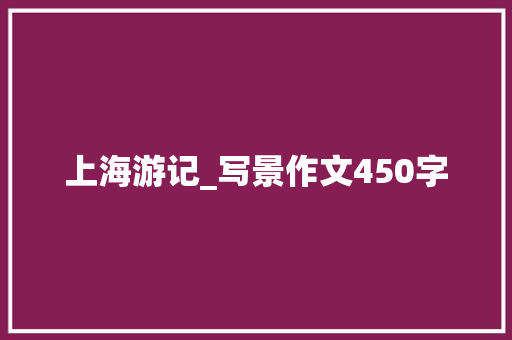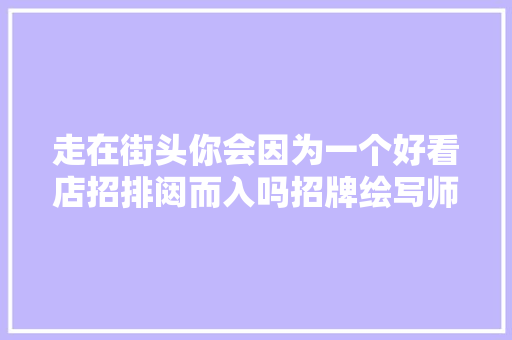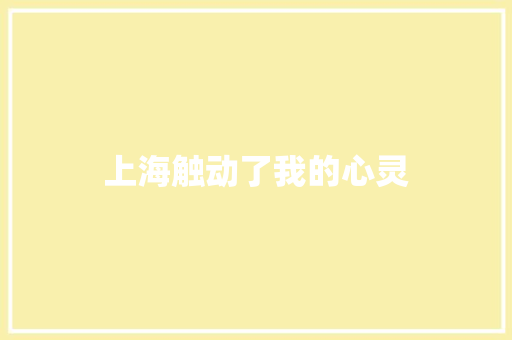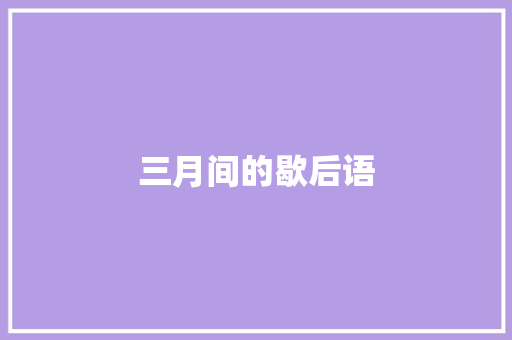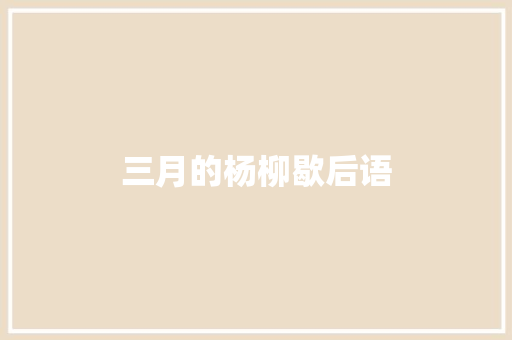本文首发在微信"大众号民谣故事,欢迎搜索关注。
提及上海,多数灯红酒绿,热闹鼓噪,熙熙攘攘,人流攒动。提及戴荃,我们更随意马虎想到的则是那首随处颂扬的《悟空》,并附上一句“我要这铁棒有何用”的戏谑调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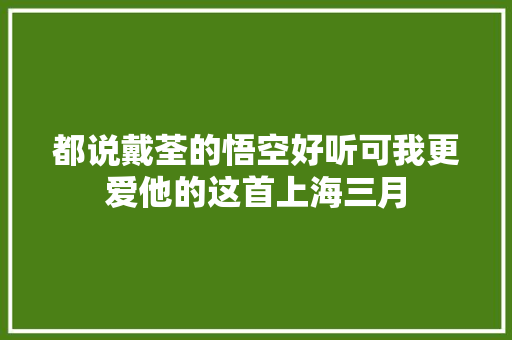
说回我个人,一贯不喜上海,大概是生活在此处的压迫感与异域感,使它在我印象中很像一个充斥了冷漠与残酷的困兽场,极度缺少人情味。
直到不经意间,听到戴荃的一首《上海三月》,让我开始思考:一贯以来,是否自己过分忽略了这座城市的美好。
于是乎,试着按图索骥,回顾起关于上海的点滴。也曾走马不雅观花似的,将上外洋滩、南京路、城隍庙、豫园、田子坊、思南私邸,以及远在松江的泰晤士小镇逛了个遍。但除了留下一些猎奇照片,彷佛也并未曾让我对这座城有更深理解。
倒不如那张各类颜色盘织交错的上海地铁图,更让人印象深刻。就在堪称这座城市最具良心的地铁里,拥挤着那些各色各样的、南来北往的陌生面孔,就像是一个个散布在这张巨大地网里的眇小粒子,在移动,或者被移动。
呼啸而过的车身随着风与轨道的摩擦,还会产生轻微的晃动。那声和力量交织在一起,仿佛是想摇醒着什么,又仿佛只是想和车厢中的人来个大略的互动。匆匆忙忙的人们来了又走,很少人会勾留,也极少人能够留的下来,匆匆,也只是匆匆。
闲敲棋子,喂茶话家常
活在一代人影象中的上海,既有十里洋场夜夜笙歌,也多家长里短的弄堂趣事。
很喜好鱼蛋叔和小陶虹主演的《赤色》,抗日买菜共一色的上海同福里戏院,噜苏日常都变得优雅起来。乃至连噔噔的高跟鞋声都散发出一股子恋爱的“酸臭味”。
裁缝和剃头匠的打打闹闹更是有趣,本日为点儿热水拌拌嘴,来日诰日又为喜好的女人醋一醋,吴侬软语地吵一吵,烟火气不要太浓的。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面这样写道,“每到这薄暮时候,总有一个卖蘑菇豆腐干的,到这条衖堂里面来叫卖……他们在沉默入耳见那苍老的呼声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随着那呼声一同消散了。这卖豆腐干的切实其实便是韶光老人……”
听戴荃的这首《上海三月》也是一样,悠悠岁月飘荡,仿佛当下就能回到那烟雨飘摇的吴地小巷。弄堂里各家烧水做饭,洗衣打扫,自行车叮叮当当地穿梭扭捏,大人们相互打着呼唤,孩子们追逐着嬉戏打闹,不远处传来几声挑担子 “馄饨面”的吆喝,家家豆浆大油条,白粥小笼包……
沪上三月春雨几场,莓茶刚刚好,闲来无事,闲敲棋子,喂茶话家常,日色、车马都很慢。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东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江湖飘零,心腹难相逢,已然是大不幸之事,更可况天人两相隔。
“记得那个三月,我踩着上海的街灯走着那条不认识的路,借住在朋友的空房里独自做着音乐,喝着不知从哪儿抓来的莓茶包,默默看着窗外,脑海里充满着无尽的旋律;
那个三月,我从窗外的稠雨望过去,仿佛瞥见那个著名的酒店中爷爷和奶奶的婚礼;也是那个三月,不知道吃了什么鬼东西食品中毒,一个人跪在床上疼到天亮;
还是那个三月,我永久的离开了一个人……2014年的三月,我执笔用歌记录了下来。”这是戴荃写《上海三月》的灵感小札,反过分来再看看歌词,一句“永夜莫过心腹难”更是沉重万分。
残灯照孤影,雨潺窗外寒,茶凉无知己,永夜不得眠,时隔经年,恍然如梦,多少很多多少风雨,借问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上海三月》这股子抹不掉的落寞与情愁也终于找到了源头。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
乍暖还寒,春雨绵绵如丝。
模糊约约记起来,年少时极其喜好的泡桐花现在也该当繁缛欲垂。只是想想,老家的数棵孩子们怎么抱也抱不住的老桐树早已被砍去,就连那座被根系蔓延到我床底下、曾生出小泡桐苗的老屋子也早已不在,不由伤心起来。
寒食已至,苍天雨细风斜,徒增料峭之意。盈虚终有数,疑是故人来。
- End -
文 | 钱爻
编辑 | 王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