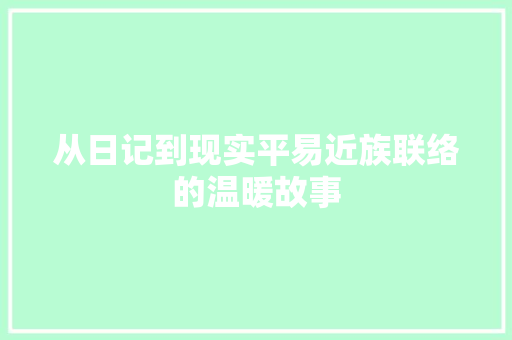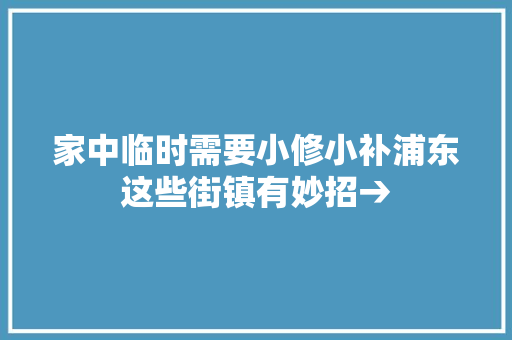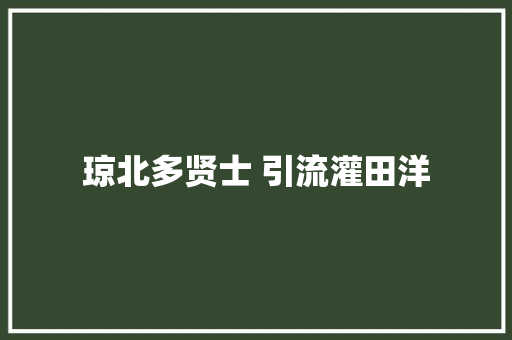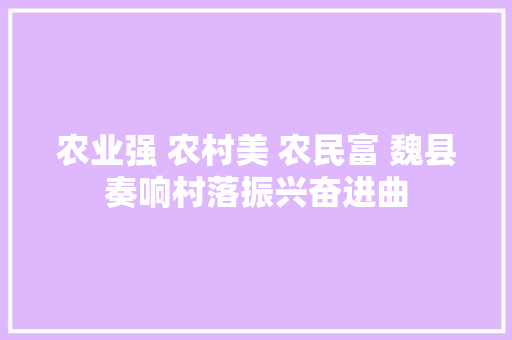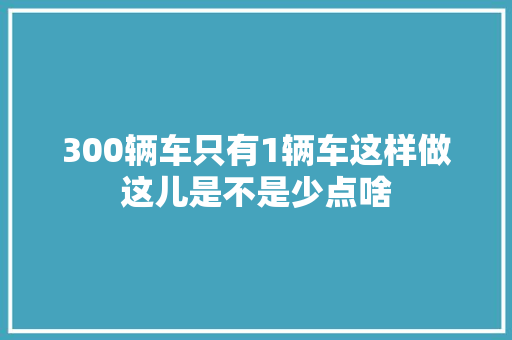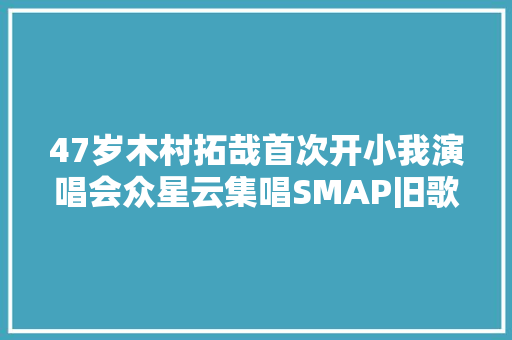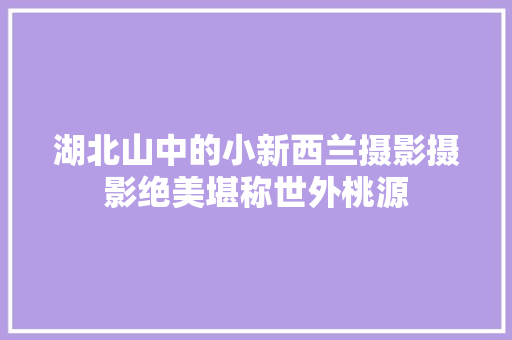伴随中国城市进程化的急行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村落庄正在迅速消逝,伴随而生的浩瀚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逝。在西安市,有一群文化人正在日以继夜地劳碌着,他们想赶在村落庄消逝之前,把村落落的人文历史、乡乡俗情记载下来。他们在野外稽核的过程中,有喜有乐、有悲哀也有收成。经由多年来的奔忙劳碌,他们写出了一本本村落史。这些沉甸甸的“纸上建筑”,成了村落民们和社会各界爱不释手的“金娃娃”……
村落落即将消逝,修村落史势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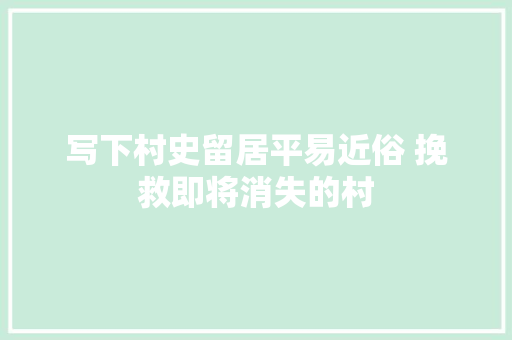
在中国的区县版图中,位于西安市南郊的西安市长安区,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地方。长安区原名为长安县,古代曾用名长安县、杜陵县、万年县、大兴县、咸宁县。这里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京畿之地,这里更是杜如晦、杜甫、韦应物、颜真卿、李密、冯从吾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的老家故宅。长安的文物古迹灿若星辰,有周代的丰镐京遗址、阿旁宫遗址;有兴教寺、华严寺、喷鼻香积寺等四十二座寺院。而这些名胜古迹,如今大多坐落于安静的村落之中。
近年来,城市开拓的大潮席卷全国,很多城市都进入了扩展冲动,西安也不例外。长安区的村落落比起其他地方,消逝的速率愈甚。“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在唐朝之前中古期间,现在的长安区一贯都是都是都城的京畿之地,如今,这里成为省会西安的南部新区。自西安市高新区设立、长安撤县设区以来,在长安的地皮上,十几年来先后培植了长安通讯家当园、高新区技能开拓区、郭杜教诲科技家当开拓区、长安大学城、西安国家民用航天科技家当基地、常宁新区、沣东新城、沣西新城等一系列新区。这些新区,无一例外地都占用了长安区的地皮,加速了村落落的拆迁。
如今的村落庄不比往昔。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打工,村落夕照益凋零。村落里的小学废弃了,不少村落里的文物——石狮子、石佛像、拴马桩,都不知时候被贼娃子偷走了。更有很多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三下五除二把家里雕梁画柱的老宅拆了,那些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都便宜卖给了别人。
马喜云的老家在长安区五星街道共同村落,村落庄紧邻洨河,自然风景幽美,过去的河里鹅鸭成群、鱼儿嬉戏,河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芦苇荡,春夏绿帐随风起伏,秋日芦花飘荡似雪,好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2010年,长安通讯家当园在共同村落户动工,村落里开始统计人口、丈量地皮、赔偿安置。区里来的干部说,几年之后,这里连同附近的几个村落庄都将变成一个崭新的园区,复兴、华为之类的大企业将纷纭入驻,这里将会成为大西安的一个新兴家当聚拢区。
轰隆隆挖掘机进村落了,一棵棵的老树倒了下来,一间间的土坯老宅倒了下去。前几天还有的一座老庙,几天之后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路。挖掘机轰鸣作响,不仅仅是推到了老屋子,也让村落里民气头一震一颤,扑腾得难以安宁。村落里的老汉们都惊呼村落里的变革太快:“这发展速率,比火箭都快!
”
村落里人们用饭爱赶“老碗会”,用饭时节,每人端出一只大老碗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街道上围作一团,或坐或蹲,或站于道旁,一圈人一边“呼噜呼噜”喋饭,一边谈天说地、东拉西扯。好不惬意!
这天的“老碗会”上,有人感叹了一句“哎,这过不了几年,咱就谝不成了!
村落庄眼看就要拆完了!
”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共同的伤感,有人回顾起小时候下河捉螃蟹,有人讲起别人在中学的初恋,有人提及爷爷讲过的传说,大家共同的觉得是,假如能把旧光阴记录下来,该有多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村落里的支书王德云和村落委会主任朱雪峰调集村落委会班子成员开了个会。大家一切磋:既然村落庄留不住了,那就把影象留住吧!
这么一来,修一本村落史也就被提上了议程。
说到修村落史,人们自然把目光聚拢到马喜云身上。马喜云原共同村落最威信的“秀才”,他当了十几年的的小学校长,村落里的大人小孩大多是他的学生。2009年,他被抽调到区政协参与了《长安百村落》村落史集的编写,他有这个履历、上风。几做生意议,以拜荣强、马西云为核心的编辑团队组成了。
村落庄看似不起眼,但随便哪个村落都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写呢?拜荣强和马喜云制订了一个体例和操持。他打算先从村落落的由来、村落民姓氏的溯源、历史沿革、文物遗存、经济发展、村落里名人、村落中人口、家宅留影等几个部分写起。
光是这共同村落的来历,原来都大有讲究。马喜云查阅清朝的老县志,得知村落庄原名叫王通寨,在文革中,由于要“破四旧、立四新”,村落委会于是从毛主席语录中取出“共同”两字作为村落名。
细心的马喜云先后搜集了村落里的三皇庙、老爷庙等古建筑的变迁历史,以及村落里现在遗存的壁画、石雕等文物。他们还从村落里老司帐刘振贤的手上找到了不少村落集体的账本,这些账本详细记载了村落里历年来的变革。
韶光一每天过去,马喜云他们的事情也一点点显出成效。一个清晰的村落史脉络被理了出来,在这份《共同村落大纪事》中,详细记载了共同村落几十年来的变革:
1954年:村落里互组组、互助社;1955年:扩社,组建高等互助社;1958年:成立公民公社;1968年:进入文革,村落里安置上山下乡知青;1975年:村落塑料厂产品打入广交会,出口国外;1980年,实现包产到户;1999年:外部公司租用村落南部地皮;2009年:共同村落小学被撤并;2010年:创安通讯家当园在共同村落户动工;2012年:村落地皮评估开始,启动“村落史影像”编撰…… 挽救性编写,让村落落变成村落史影像
长安区五星街道间隔西安市二十多公里,如今已成为西安的近郊。马喜云说,附近有不少村落庄由于工业园区用地被拆迁后,村落民失落散,原来每年要搞“三月三”的庙会都搞不起来,只能建了个QQ群,来延续昔日的乡情。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过去的人望乡、乡愁还有一个载体,如今连村落庄都没有了,如何向子孙后代先容曾经的家园呢?流落去四方的人们,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
如此一来,修撰村落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显现了出来。如今的数码影像技能发达,马喜云等几位编委会成员经由切磋,决定以大量的图片形式来展现共同村落的历史。他和村落司帐李西平,几个人跑遍了村落中的几百户人家,家家户户全部访问到,搜集老照片、老故事。固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陆续搜集来了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文革时候的照片,以及村落里搞社火竹马、婚丧嫁娶的风尚照片。有时候为了核对一张照片的详细年代,就要拜访很多人,反复核对。
马喜云走村落串巷,拜访家里有老物件的庄家,外的惊喜就在这细致的察访间涌现了!
有一次,他去找一个心灵手巧的媳妇,拍她剪的“鞋样子”、绣的花,这样的手工劳动险些快从屯子绝迹了。就在他拍摄的过程中,创造这家的墙角有几卷发黄的书。打开一看,居然是村落里张姓人家的家谱,还有几份解放前的地契、清朝的农历书!
这些创造让马喜云欣喜若狂,有了这些实物证据,就能更好地阐述,过去的人们是怎么样在这片地皮上生活的。
村落史写作,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村落民的合营。村落干部刚开完动员会,村落里就有人说闲话,说“出什么书,怕是有人是和村落干部合资弄钱呢!
”马喜云听见后,也不阐明也不生气,他以为自己既然接管了村落里的委托,就得把这本书编好。毕竟,对付整天“修理地球”的村落里汉来说,出书和被书本记载,都属于比到月球还迢遥的事。
村落民张红中家里有一副过去耕地用的三脚耧,在二十多年前,人们到了秋日耕种麦子,就会给耕牛套上辕,拉起三脚耧把麦子种到地里。如今播种机器化之后,三脚耧就没了用武之地。很多人家把它劈柴烧火,一焚了之。马喜云找了张红中三次都没见到,第一次他家人出去赶集了,第二次是去走亲戚了,又一次是他进城打工去了。爽约三次之后,马喜云在他家等到入夜,终于等来了这家人。问清楚他是来拍三脚耧的,张红中哭笑不得:弗成就把这物件送给你嘛!
还劳烦你跑来这么多遍!
马喜云知识分子出身,善于讲道理。他不苟言笑地讲:“这耧和耙,都是先人留下来的好东西。你以为你利用着未便利,这过去的工匠费了大力气才造成。往后农业都机器化了,村落里没有了农具,娃娃们终年夜了,哪里还知道以前的农业、屯子呢?哪里还知道‘汗滴禾下土呢’?”
马喜云教过张红中,也教过张红中的儿子。一看老师真生了气,张红中匆忙赔罪:“马老师别生气!
我们粗人看不了你那么远,不过,你咋说我咋合营!
”马喜云给他家的犁、耙、耧都拍了照。看自己的老师如此负责,张红中深受冲动,从此志愿做了老师的助手。
让马喜云非常惋惜的是,很多老人节制了大量的民间掌故、口述历史,他们朽迈的速率,远远比那些老屋子更快。2013年7月,马喜云理解到邻村落有个90多岁的老婆婆,她对附近村落落的演化历史最清楚,对付60年代乃至更早的人口迁徙、饥荒岁月都熟知详情。马喜云骑了辆自行车,来到村落里来找她。不巧的是,老婆婆恰好生病了,正在家里挂吊瓶。她苗条而瘦削的脖子一阵一阵抽搐,说话都很困难。马喜云有点不忍心,就给老婆婆拍了几张像,越好过两天再来采访。
两天后,马喜云再来找老人。却得到了一个震荡的:老婆婆已经去世了!
老人的孙子见告他,在马喜云走的第二天,老人就去世了。这经历了一世沧桑、一肚子村落庄故事的老人,就这样匆匆走了。她的拜别,给马喜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也匆匆使着他,得更加努力更加迅速地搜集资料。
在编撰《共同村落史》中,别具匠心的创意是,给村落中的每家每户都放上一张照片,一样平常来说,家里有几口人就会在家门口照个合影,这也得到了村落民们的热烈相应。几百户人家,这个拍照的事情量不可谓不大。如今村落庄被拆迁,年轻人大多数外出到西安打工,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照、百口福就变得很困难。有时候,马喜云跑了好几趟,都拍不到一个家庭的百口福。
后来,受到马喜云感召的人越来越多。村落里的年轻人们拿来了村落小学的班级合影,老人们翻出来70年代给生产队赶马车的照片,还有人送来了村落里的老粮站照片,改名贵的是,村落民们找来了不少反响过去生活风尚的照片:有五六十年代嫁妆实木漆花的衣柜、桌子,有七八十年代的嫁妆缝纫机、收录机,有村落民们热热闹闹赶庙会的场景,也有春节期间村落里唱大戏、老少爷们人隐士海的老照片。
老生产队长、老支书、老妇女主任、老干部、老西席,村落里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他们的照片一张张找来了,他们链接着村落落的发展;村落里的大桥、河流、农田、工厂、绿地、村落舍、玩耍的孩子、跳广场舞的妇女、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蒸米皮的老婆婆……村落落的历史,都随着摄像机的快门声,一张张被记录下来。
半年往后,一本10万多字、200多张插图的《共同村落村落史》正式付印。2012年春节前,当村落里的大喇叭开了腔,喊村落民们来村落支部领书的往后,宁静的村落庄里顿时炸了锅。村落民们手捧着全彩印刷、装帧精美的村落史,纷纭掩饰笼罩不住激动和惊异。有人说“好我的爷呀,没想到咱村落还有这么多历史!
”,有人说“哎呀!
喜云真是细心人,连生产队的账本、旧社会的织布机都能找见!
”
一本村落史,留住了永久的乡愁
在修村落史中,马喜云搜集到不少正能量的故事,他不惜笔墨,把这些故事记录了下来。
在给兆丰村落修村落史的过程中,他记录了村落中一位从事殡葬礼仪的老人张新民。张新民识文断字、能书会画,一样平常人都忌讳办丧葬这个行当,但张新民却干得有条有理。老汉今年80岁,依然能写挽联、棺材彩绘、墓穴壁画,给亡人写祭文,葬礼的10个程序他仍旧能搞得井井有条。如今,老人仍旧是声音洪亮,精神抖擞,操办起丧礼,指挥几十上百人一点都不乱。
兆丰村落有个媳妇叫鲜小艳,自从她嫁到村落里的李家后,就肩负着照顾从小双目失落明的叔伯哥哥,这盲人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是她来打理,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委实不随意马虎。村落里人常常看到,那失落明的男人拄动手杖走街串巷,穿着干净、衣着整洁,大家都夸奖这是好媳妇鲜小艳的功劳。
村落里过红白喜事掌勺的大厨、救去世扶伤的赤脚年夜夫、身残志坚空手发迹的上进青年、发挥余热帮助公益的退休干部、克尽孝道的“五好家庭”……在马喜云的笔下,村落里人们口碑相传的正能量故事,被持重地记入了村落史,这既是一份名誉,也是村落民们对他们的认可。
既然是修村落史,当然要有严明性。马喜云说,也不是所有送来材料都如数照登。核对村落中历史事宜和历史人物的情形,他以老县志和州里能找到的文件为准。对付暗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故事、传说,他基本上都是忍痛割爱,不予采取。“这就相称于,我们采取的材料,一样平常是采取‘正史’,而不是采取‘野史’,不准确、不能多方验证、不能说清来源的资料,我们不用。”马喜云说,别鄙视村落史,再小它也是一段历史,牵扯到历史,就没有小事。
马喜云编辑团队的几本村落史,在附近的村落落间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共同村落有个老汉,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外地事情。老汉看了村落史,找到村落干部哀求再买五本,他说,他要给每个孩子留一本,让孩子们不管走多远,都得记住根在这!
印了1000册的村落史,三天之内就被村落民们领完了。大家纷纭反响要加印,开过年后,共同村落把村落史又加印了一次。采访中,马喜云见告,这几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先后为附近5个村落写过村落史。这些人基本都是各村落里的“文化人”,有退休的西席、干部,也有村落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帮忙。每部村落史付印后,都深获当地村落民的好评。2015年,他还将会有几部村落史付印。“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本日,修撰村落史有着极为主要的意义。我国的村落庄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歌曲、舞蹈、仪式、武术、厨艺、古建筑,随着村落落的消逝,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正在加速毁灭。这将会给我们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灾害性的后果。”陕西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梁荫说,修撰村落史抢救性地保护了民风民俗,让人们有了可以触摸的历史,节制了打开村落庄影象的密码。
令人振奋的是,目前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开展修村落史的活动,很多地方政府都将修撰村落史提升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公益活动。在台湾省彰化县,于2005年启动了“大家来写村落史”的活动,这里的“台湾社区营造学会”乃至专门出版了书本,辅导大家怎么样一起来动手修村落史。在他们的《大家来写村落史》的媒介中说到:“台湾社会的发展与转型能否健全,蜕变是否顺利,如何重修与发展社区,文化彷佛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有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寻衅大历史,凸显草根史”。重视村落史、小区史是人们历史意识增强和社会进步的表示。
村落史作者马喜云在采访结束时呼吁:希望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来参与村落史的编撰,尤其是村落中的退休西席、离退休干部,更适宜来做这份事情。一来是可以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二来修村落史确实是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每一本村落史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纪念。马喜云说:目前,全国各地编撰村落史都是各按各的来,没有统一的格式。这也就造成了很多村落史编撰得头重脚轻、比例失落调。因此,他建议再动手编村落史之前,村落里的知识分子们不妨先多找找同类村落史,定下大家都满意的编辑体例;其余要多查县志和官方文件,只管即便以公开拓表的文献为准;第三便是要群策群力,广泛发动群众,让父老乡亲们都参与进来,人多力量大,编出来的村落史也就更靠近完美。(曹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