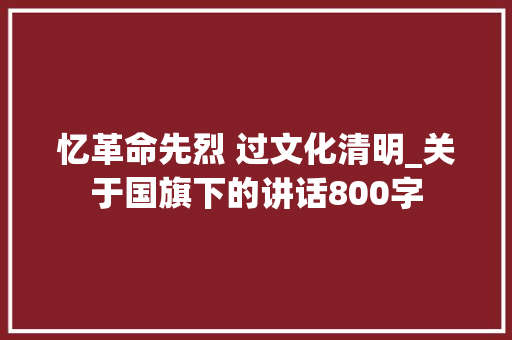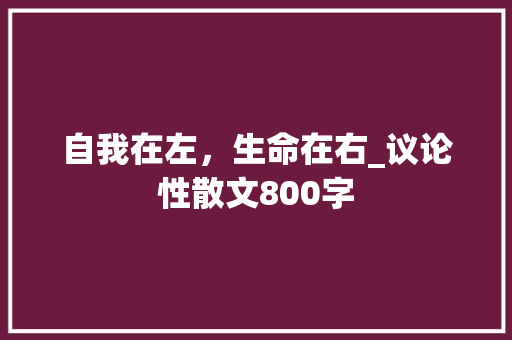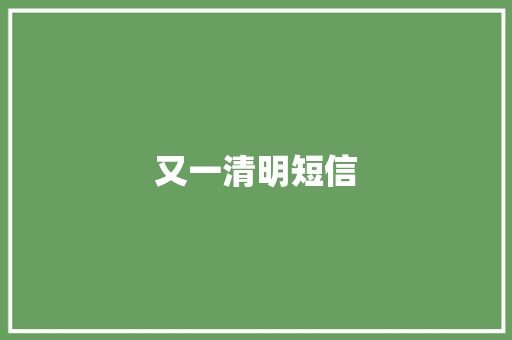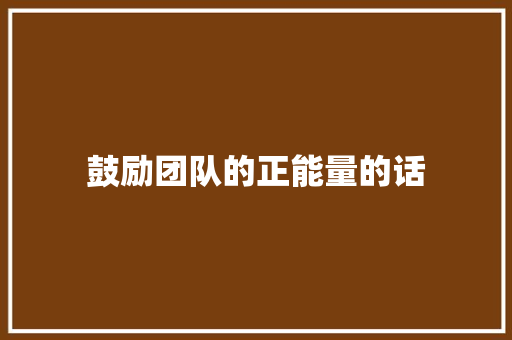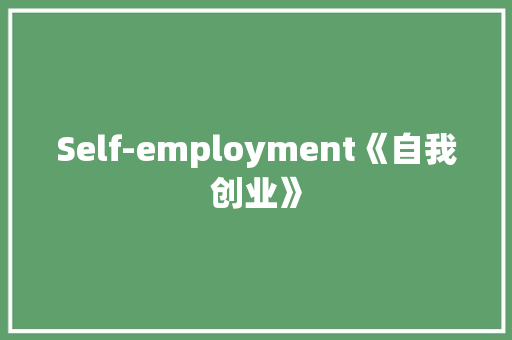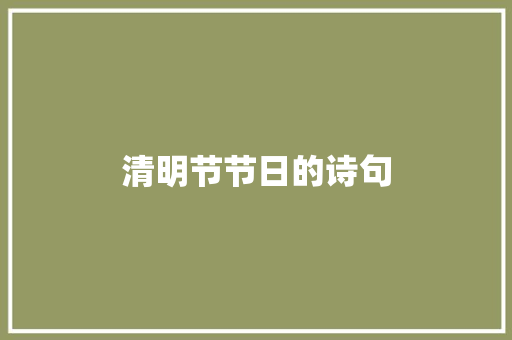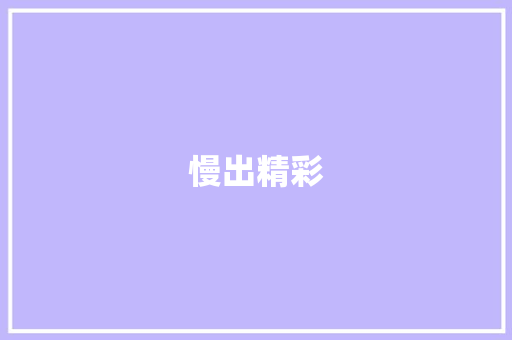芳草凄凄,山景如画;穿行其间,把酒言欢。这种场景之中诗人们找到了快意,找到了自我。在自然中行走,诗人们揣在怀里的是酒,喝在肚子里的是兴致。没有酒气的行走纵使好景怡人,也是索然寡味的。王禹偁在《清明》中把这种情绪描写得甚至有些悲哀的意味: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因此,世人离开尘世去踏青也并非为看山看水,倒意在寻找自我。在尘世中的自我是失去独立的自我,让现实的俗态和繁琐所蒙蔽,活得越是繁忙与精彩,越容易找不到自己。因此,诗人丢下笔,带着酒去自然之中寻找原生态的生活和本来的自我。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暂时地离开了尘世,回到了自然的拥抱中。但当他从郊外又回到现实,一切仍属于自然,仿佛仍没有找到自己: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所以,自然给了他们力量。
清明时节,诗人突然要抛开现实去寻找自己,找到自我在哪里的确证。除了桃红柳绿之外,他们看见的还有一个共同的意象便是坟墓。坟墓寓意着人生的句号,却也是人类的根源,是人烟延续不断的节点。有了坟墓便是有了前世的证据和后续的根本。因此,与其说诗人们是去自然之中寻找自我,更不如说是去寻根。高启在《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中说: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没有子嗣的坟墓是令人悲哀与恐惧的,这是最伤感的事情,纵是有美景如画,只能是让人更生心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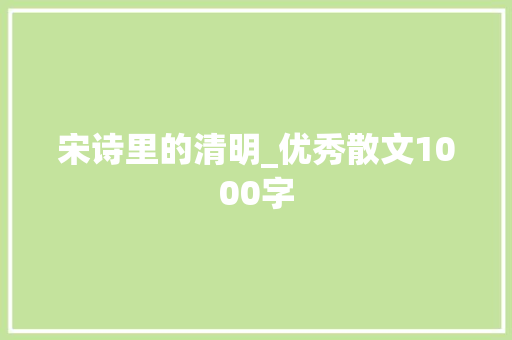
其实,岂是独独的诗人心寒。于国人而言富贵贫穷不足道,倒是上没有祖宗根源,便要被骂作从树丫上掉下来的野种;下没有子孙,便要被骂作绝八代的人家。这些绝比金银财宝、王侯爵位来得重要。当然,也有子孙满堂却悲凉无尽的,高翥在《清明》中所述就让人感慨万千: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读宋诗,念清明。几行文字只不过是几千年过一个节日的缩影。国人看重清明节,在乎的不仅是草长莺飞的美景,更在乎在思考与记忆中找到并守护自我和根源。这是清明的要义,也是几千年香火不断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