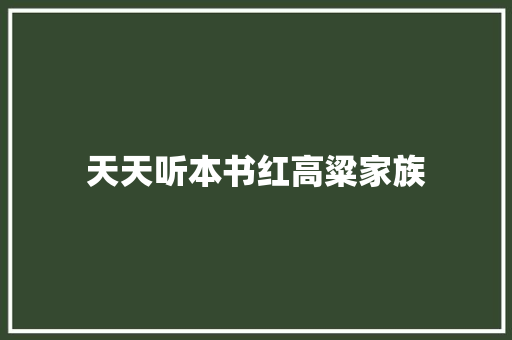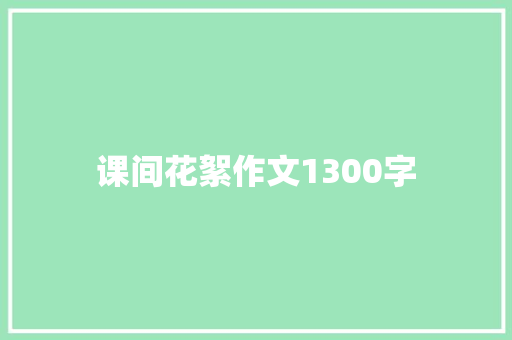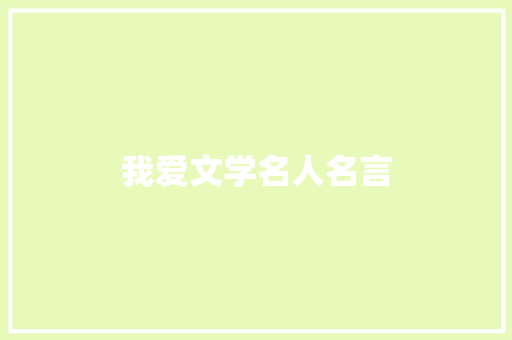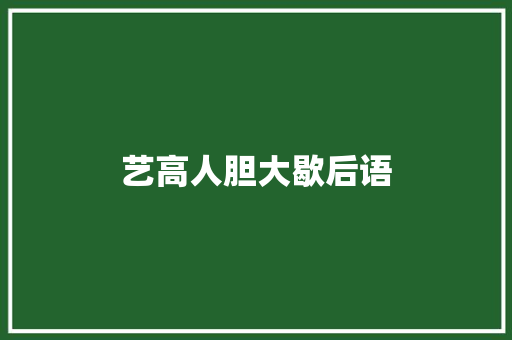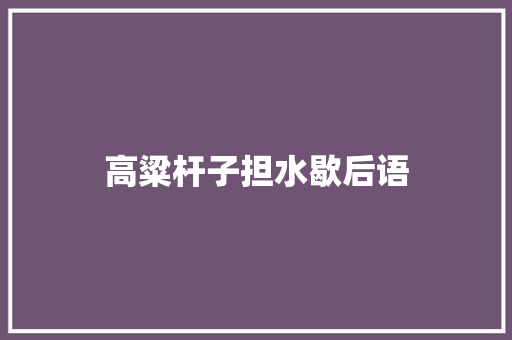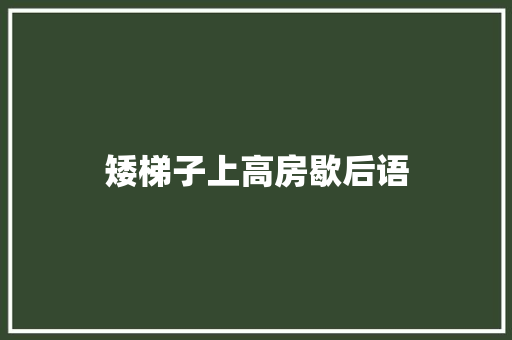人物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揭橥作品,1985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公民文学》杂志揭橥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2011年凭借小说《蛙》得到茅盾文学奖。2012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领悟在一起。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繁芜情绪,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备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措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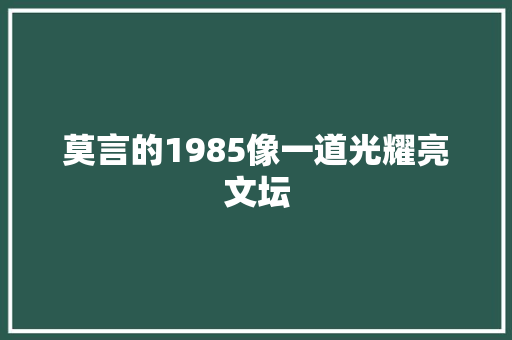
莫言是笔名,真名管谟业。谟是打算,也是谋国事的一种文体。莫言21岁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24岁调到保定,任政治文化教员;保定成了他创作的摇篮,他最早的小说都揭橥在保定市的《莲池》上。1983 年在《莲池》上揭橥的第四篇小说《民间音乐》,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篇小说帮助莫言离开了保定。它先得到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长西席的讴歌,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与孙犁的评论,到北京报名。
《透明的红萝卜》揭橥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揭橥后专门开了漫谈会,真有一下子耀亮全体文坛的觉得。我后来才知道,创作冲动实在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小小年纪就被侮辱的凄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因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晶莹透明,泛出金色光芒的萝卜,觉得太强烈了。那萝卜飞出去,就划出一道俊秀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付艺术之浸染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的,乃至令人震荡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年夜的油画般的觉得。
随后创作的《球状闪电》《爆炸》,连续表达情绪无奈与村落庄的压力。小说开头,莫言写“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勾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喷鼻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授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肃静,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慢动作般写这记耳光,我记得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稿纸。这是家庭压力的象征。
莫言在1985年的姿态,是要逆那些一环环讲线性故事的方法。他说:“没有故事便是最好的故事。”他以大量触觉光鲜的觉得支持绵密的阐述,他写麦秸在阳光下爆响,到处都反射着光芒,使“所有颜色失落去颜色 ”;写“尖锐的麦芒上生着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相互摩擦,沙拉拉响”;将蝉噪喻为“炮竹的裂片,碎片像雪片在空中浮游”。光荣、音响、味觉如霰迎面而来,真是想象力恣肆。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阐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怖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彷佛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伸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那时约稿叫“订货”。一个精良作家“井喷”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部。《红高粱》由此揭橥在1986年第三期《公民文学》上。小说以第一人称“我”阐述“我父亲”、“我奶奶”与“余司令”,这样可以突出主不雅观感想熏染,更主要因此主不雅观感想熏染超越情节。情节从14岁的“我父亲”随着余司令的军队去伏击日本汽车队始,但结尾才用三节篇幅浓墨重彩写伏击。第一节先用整整一节写高粱地这个传奇发生地的意象,他形容八月深秋,“无边无涯的高粱红成洸洋的海洋”,然后写高粱地里的雾气,写天地间弥漫着高粱的赤色粉末。洸是水光,洸洋是水无涯际,正是莫言对高粱地这样动人的描写冲动了张艺谋,也使他往后的电影里,再离不开这种繁茂的鲜绿了。
构造上,莫言是先从罗汉大爷写起,写“我奶奶”与他暧昧的悬念,写罗汉大爷本可轻松逃脱劳役,却因他家的骡子而被打成血肉模糊,然后大义凛然地被凌迟。中段才写“我奶奶”被颠轿,余占鳌制伏了劫路者,却故意不写余占鳌如何成了“我爷爷”,反而插出来一个说“大英雄自风骚”,昂首阔步走过余占鳌从背后射来子弹的任副官。末了,才集中写那段“我奶奶”回外家路上,与余占鳌荡气回肠的野合,写畅快淋漓的悲壮结尾。这个阐述构造很显示莫言的大气:罗汉的凛然,“我奶奶”在被劫时大大方方跨过轿杆,站在矢车菊里烂漫的笑,乃至任副官头也不回同样凛然地走,都是为末了三节做铺垫。他要在“我奶奶”去世前,才写她与余占鳌野合时,“炽目的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的觉得,这阳光与鲜血迸射染红高粱的结尾整合,他追求的是“大沟壑、大抱负、大气候”,情节只是气垫。
《红高粱》是莫言创作的第二个台阶,一揭橥就好评如潮。张艺谋打算将它改成电影是1987年秋的事,那时他在帮吴天明拍《老井》,演主角。牵线的是影协的罗雪莹,由于莫言自己不愿改剧本,就请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与我互助。陈剑雨是我在《公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们的女儿,便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张艺谋的习气是先侃剧本,在我当时白家庄二十多平方米的家里,张艺谋一次次从《老井》的外景地赶来,盘腿坐在我家沙发上,人精瘦,两眼放光,聊到愉快处常常忘乎以是,喜逐颜开。他太喜好小说中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我奶奶”,“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成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
当时聊得最激动的是有关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那时很推崇日本一个导演一部拍芦苇的电影,我们一起用我家的录像机看过那电影,那种暗暗的光,风吹芦苇优柔摆动的绿美极了。张艺谋说,末了打仗的戏必须简化,“由于没有好的烟火师,八一厂就那些人,就那么几个炸点,绝对拍不出壮不雅观的场面”。以是,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我记得,罗汉凌迟怎么表现,当初谈论很多。谈得最激动是,罗汉去世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石碾,把漫山遍野的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的残缺的高粱红了,那首歌唱起:“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这是小说里任副官教唱的歌。
但张艺谋后来到高密、东北、内蒙古去找外景地,走了一圈回来说,真是到处都找不到莫言小说中那种高粱的觉得,哪里还有那样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呢?不用说,大场景于是被否定了。听说,他末了在高密,只种了几十亩的高粱,只能拍局部的觉得。这部电影的投资,听说只有八十万。那是张艺谋的创业期。八十万,现在想,真是不可思议。
《丰乳肥臀》可能是莫言篇幅最长的小说,推动创作的是他母亲去世。在悲痛中,他要讴歌一个博大傲立的母亲为寄托,因此,56万字只用了83天,1995年春写完初稿,改了三次。
我是把《丰乳肥臀》与陈虔诚的《白鹿原》放在一起,看作反响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的两部史诗的。两部小说,都是五十多万字篇幅,沉甸甸,一部写陕西,一部写山东,映现百年中国,都极具代表性。写百年中苦难,回避不了外族入侵、兄弟相戕;回避不了前因后果,自己酿就的各种苦果。不同的是,陈虔诚以朴实、雄浑的写实,塑造了一个白嘉轩,一个鹿子霖,两人斗了一辈子,写透乡土中国的社会构造。莫言则以象征的夸年夜,强调因果交缠的苦难,在男性家长缺失落的条件下,讴歌一个在苦难中茹苦含辛,维系家族生生不息的母亲。“丰乳肥臀”是生殖力,农耕社会家族枝繁叶茂的根本。不“丰乳肥臀”,就不敷以喂饱、养大、呵护这么多的子孙,以是,它是坚毅而兴旺的生命力的象征。母亲的胸膛就如洞开的广袤的大地,她不是现实中的母亲,莫言生活中的母亲,实在很瘦小。
莫言实在是浮夸了生殖对母亲造成的苦难,来写母性之伟大。传统中国,传宗接代是女子的第一要务,因此,小说中聪慧的鲁璇儿一嫁到上官家,就变成上官鲁氏,没有了自己,只剩下维系上官家繁荣的职责。故意思是,这部小说中没有父亲:上官寿喜没有生养能力,寿喜的父亲福禄也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于是,上官鲁氏要繁荣上官家,就只能借种:从姑父到强盗、江湖郎中、屠夫、和尚。
莫言塑造了一个朴实、坚忍又内在刚烈的母亲。成为生殖机器,接管一个个女儿的选择,收受接管她们扔下的各种身份的孩子,她都是无奈。一介草民,她无力改变统统,只能承受统统,将绳深嵌在皮肉里,拉着家这辆破车,不断躬身前行。她说:“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去世,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去世,去世随意马虎,活难,越难越要活。”这种活下去,且要记住的朴实,使她在战乱中推着木轮车,两边篓子里都坐着孩子,“两只小脚在冰雪中成了两个小镢头”;三年困难期间偷将豌豆吞进胃里,回家再吐出来喂活“鹦鹉韩”的描写,格外动听。母亲的光彩,尤其展示在那个大叫着“我要找我的孩子”,昂首走向磨坊的形象中。她顶着马排长的枪口,打了他一记耳光,轻轻地问:“你有娘吗?你是人养的吗?”在射来的子弹中,拔开了大门的插销。
莫言因此体量确立作品的主要性。他至今为止创作的长篇,体量最重是《丰乳肥臀》与《死活疲倦》。两部呕心沥血之作,论篇幅,《丰乳肥臀》排第一,《死活疲倦》少近十万字。论容量,《死活疲倦》的密度可能赛过《丰乳肥臀》,个中隔了十年。跨度上,同样写半个多世纪,《丰乳肥臀》的线性阐述,到《死活疲倦》变成一个循环的空间。
这部小说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讲1949年土改,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一贯在牲口道循环:从驴变成牛,牛变成猪,猪变成狗,狗变成猴,经猴才变成大头婴儿“蓝千岁”。之以是一贯在畜道,是由于他总喊冤,不愿忘怀痛楚与仇恨。本来,投胎前,喝“孟婆忘魂汤”就可忘却统统,但他拒喝或说那汤于他没有浸染。他沉溺于过去无法新生,于是只能勾留在“西门闹”的情境中。小说第四部《狗精神》的结尾,阎王问他:“现在你心中还有仇恨吗?”阎王说:“我们不愿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以是,就让他再转一次猴,“把所有仇恨发泄干净,再重新做人”。这是有关循环,一个很深刻的角度。《死活疲倦》是莫言获诺奖的,一块决定性的基石。
《蛙》是莫言至今为止的末了一部长篇,写成于2008年,在《收成》揭橥后,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给这部小说写的后记标题是“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辛弃疾西江月词中的句子:“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喷鼻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以这首词读这部小说,故事若放在词意中,会增长痛惜悲哀。这部小说写屯子粗暴实行操持生养酿就的悲剧及时过境迁后的荒诞。莫言因此蛙写娃,塑造了一个传奇的姑姑形象。他在后记里说,生活中,他确有一位妇科年夜夫的姑姑,接生了数千婴儿,亦有“为数不少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短命在她部下”。莫言借此姑姑承载操持生养这样的大事宜,以蛙与女娲的“娲”为意象。
2012年,莫言以他三十年费力累积的辉煌造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打算一下,从1981年揭橥第一篇习作到2012年获奖的三十一年,他写了约六百万小说,三百万字散文随笔杂文,总计九百万,在中国新期间作家中,累积篇幅之多,题材面之广,整体所具之深度,获奖是他费力的赠送。他在三十年里走了别人可能要用五十年走的路,是实至名归。
(本文摘编综合自朱伟作品《重读八十年代》等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重读八十年代》,朱伟著,中信出版集团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期;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天下杯转播的时期;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期。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个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