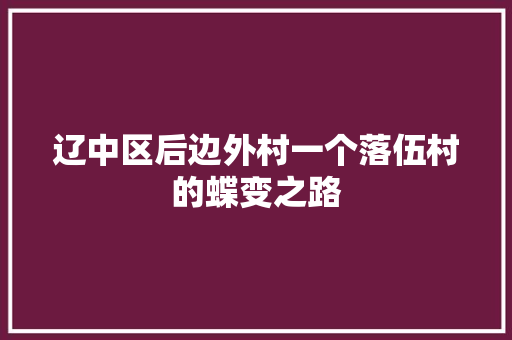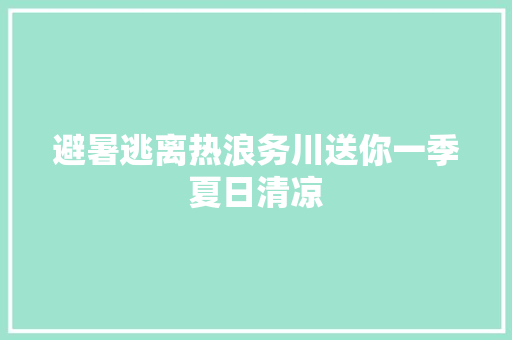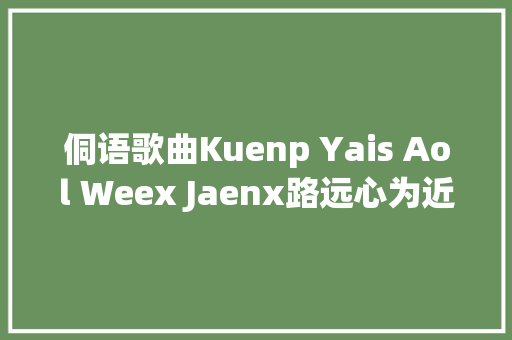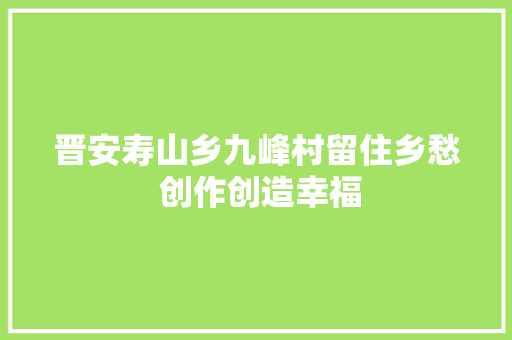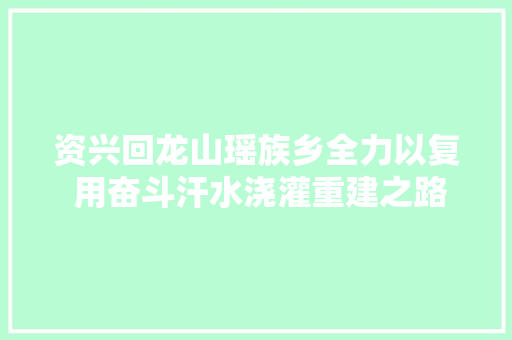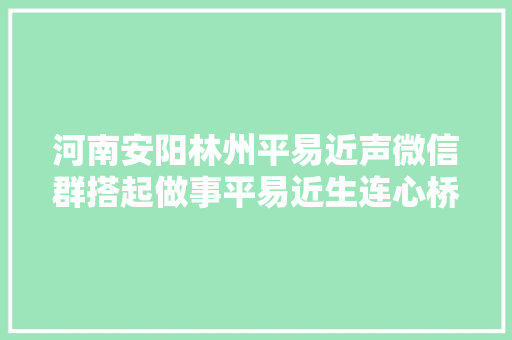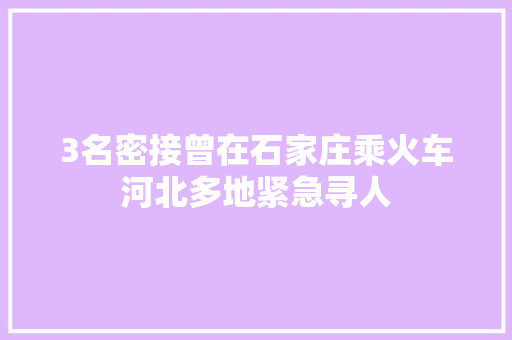▲法制公园广场上,付德顺正在架设放映机。受访者供图
6月27日,北京密云,北庄镇杨家堡村落正经历夏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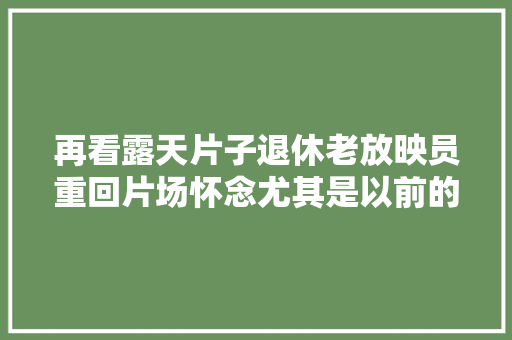
傍晚,村落里的喇叭忽然响起:“乡亲们把稳了,本日镇里文化站派‘付电影’回来放露天电影,就在村落东边的广场上,晚上没事的可以出来看一看。”
葡萄园里弯腰劳碌的村落民们直起身来。
“放电影?哎呦,我得有二十几年没看过露天的电影了吧……”村落里的老人王杖贵小声咕哝,“彷佛也有好几年没见到‘付电影’了。”
“付电影”本名叫付德顺,原是村落里的露天电影放映员。二十多年前,付德顺总背着几十斤重的放映机跋山涉水,村落里的孩子都爱跟在他身后,为了看场电影追出十里八里。
久而久之,付德顺就被村落民们称呼为“付电影”。
如今的付德顺已经63岁,退休快满三年,电影放映的“接力棒”也交到了徒弟李士龙手中。
今年6月,为庆祝“建党百年”,密云区电影中央每逢周末就在法治公园、密虹公园或是村落落广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带不雅观众重温赤色经典。已经退休的“付电影”也因此被请了回来。
有时即便放映不顺利,又或是影片已经放完,很多不雅观众还是迟迟不散场。
付德顺以为,不雅观看露天电影是一代人的独特影象,“大家都是在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
▲6月27日,正在等待电影放映的杨家堡村落村落民。新京报 薄其雨 摄
期待已久的露天电影
6月27日,晚上7点了,天色依旧通亮。
付德顺和徒弟李士龙将一辆数字电影放映车,开进群山环抱的村落东广场上。这里有几百平方米大小的篮球场,四周是绿色栅栏围挡,三三两两的村落民早就散坐在场外的健身器材上。
车靠边停稳。李士龙将设备从车厢卸到篮球场中心,师徒二人协力将两米长的幕布挂到篮球场东侧的围栏上,再将数字投影仪、音响摆放在幕布前空地处,开始连接并调试设备。
付德顺心里有些没底。村落里已经有好几年没放映过露天电影,也不知道村落干部在广播里那几句仓促的话可以关照到多少人?
师徒俩调试声音时,村落民们拿着板凳、马扎陆陆续续赶来。
他们有的围坐在一起提及身长里短;有的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上前不雅观摩放映机;有的走到付德顺阁下跟他寒暄,还有五六个孩子分享着准备好的零食,等待着电影开始。
“咱们村落得有二十几年没放过露天电影了吧?”村落民王杖贵拿着一根铜色烟斗走到人群中,嘴里依然念叨着。
“不,前几年有放过,我还跑来看来着,便是忘了放的啥电影了。”一个男孩回嘴道。
看着村落民们不断加入,付德顺以为,过去放电影的熟习觉得又回来了。
他彷佛又回到了三四十年前。挂满繁星的夜晚,他正在调试设备,身后坐着上百位村落民,聊家常、评论辩论庄稼;老人咳嗽、小孩哭闹……各种声音搅在一起。可当电影前奏响起时,场院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看电影前便是要这个样子,全村落人,乃至交几个村落庄里的人围坐在一起,这种觉得是一家人对着电视机或者一个人举动手机体会不到的。”付德顺笑着说。
那时候没有电视和手机,能看一场露天电影是村落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
电影放映员进村落的传开,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翘首期盼,付德顺回顾,“如果是自己村落庄放电影,有的人乃至会端着碗饭过来,边聊边吃,边吃边等,很是热闹。”
▲密云电影中央门口,付德顺等放映职员正在将放映设备装车。受访者供图
一年放300多场的“付电影”
这天电影放映前,不少村落民与付德顺闲聊,提起当年追在他屁股后面看电影的日子。
村落民们兴致勃勃的回顾着,每当付德屈服电影公司取了胶片回来,他们就会跟到付德顺的家中看着他检讨胶片,等付德顺推着放映机出门,他们还会一起随着走到放电影的村落庄里。
1976年到1981年,由于交通不便,没有公路,各村落之间只有大家伙走出来的波折巷子。放映机、音箱、幕布都是靠手推车送到各村落,不雅观众随着放映员走,放映员随着机器走。
久而久之,付德顺就被村落民们称呼为“付电影”。
而随着村落里的交通逐渐改进,付德顺的交通工具也在一步步升级。
1982年到1986年,付德顺可以骑着自行车放电影,车子上带着机器。1987年到2004年,政府给他配备了三轮拖沓机,放映器材都放在拖沓机上,又快又省力,一开便是十几年。
那些年,露天电影尤其受村落民们喜好。最忙的时候,付德顺一年要放300多场电影。
付德顺记得,有一年夏天,他正在放映电影《南海风云》,溘然间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他赶紧收起放映机。半小时后,雨变小了,可还有很多人躲在场院里的房檐下,不愿离开。
看着他们那种期待的眼神,付德顺又重新接上线,为放映机撑起伞,自己顶着小雨把电影放完。第二天他便感冒了,发热持续躺了四五天,“但那会我心里依然是美滋滋的。”
冬天是露天放电影最难熬的一个时令。
农闲下来的村落民希望看韶光长的故事片,付德顺每每都会一晚放两部。有次他到离乡15里的干峪沟村落放电影,由于村落里人少,景象冷,他把电影机搬进田舍院子,让老人小孩坐在炕头上,隔着玻璃看。他却在寒风中站了三个多小时,也因此落下了冻脚的毛病。
从业以来,付德顺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变革,也看到了露天电影的没落。
随着胶片电影逐渐被数字电影所取代,老百姓开始不知足于“被动地看”。
“老付,就快秋收了,给我们放点这个时令的科教片吧。”村落民看到他会提前跟他说一下需求,只要能在电影中央拷贝来的,付德顺都会只管即便知足。电影放映也由此经历了从“放什么看什么”到“看什么有什么”的转变,屯子不雅观众喜好的影片类型也随着更迭。
村落民王杖贵说,“7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看样板戏,我最喜好《白毛女》,后来喜好看《卖花姑娘》,再后来就喜好看战役片,现在还是喜好战役片。”
样板戏的时期过去后,第一部走向屯子的爱情片是《庐山恋》。“那时候村落里人看到女主人公亲男主人公时,还会惊呼,‘她怎么能亲他呢’,‘这咋给放出来了’,后来他们就逐步习气了,也没有人低头回避那样的画面了。”
当电视、网络、多媒体技能相继得到运用和遍及后,露天电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6月27日,在杨家堡村落委会数字影院,付德顺正在先容当代数字放映设备。新京报 薄其雨 摄
“老伙计”
如今的付德顺已经63岁,退休快满三年。
今年6月,密云区开启百场赤色电影展映周。每逢周末,《地雷战》《出生入死》《金刚川》等影片会依次走进社区、公园、学校、工地、敬老院、民宿村落等,讲述赤色历史故事。
付德顺因此被请了回来。
付德顺记得,事情时他整日整夜忙于放映电影,家中田地和大小事务都交给了妻子,每逢春节,都是电影放映最红火的时候,他也没少被妻子埋怨。退休后,他有更多韶光陪伴家人,却总以为日子变得空寂又漫长。
“不放电影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付德顺说。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的“老伙计”——躺在密云电影中央库房里的那些老胶片。从1994年起,密云电影中央历经8次搬家,搬一次家,老胶片就换一个新地方。
电影中央副主任李广有提及,“我们库房里至今仍存着3000余部影片,我们一部也没舍得丢。”黑白影片有《地雷战》、《隧道战》、《出生入死》等;彩色影片有《刘三姐》、《走近毛泽东》、《冲出亚马逊》等,付德顺对每一个“宝贝”都如数家珍。
付德顺也没想到还能有机会和当年的“老伙计”相逢。
为了欢迎这次活动,付德顺还和其他几个技能好手一起,去密云电影中央修复了放映机。
库房里,付德顺看到以前电影拷贝的铁箱子,箱子上蓝色的漆已经被磨进了岁月里,露出赤色的铁锈,“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公民大众的”,箱子上印着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漫谈会上的讲话》依然清晰可见。
他打开箱子,仔细检讨着老胶带和放映机的齿孔。
“16毫米放映机比8.75毫米放映机放映间隔远,画面质量也要清晰许多;溴钨灯泡光源好,提高了放映质量,却让夏日傍晚的蚊子准确地找到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双机放映办理了换片时的断档,再也听不到一卷胶片结束时,人们由于不雅观影过程被打断而发出的抱怨声。”对付这些“老伙计”,付德顺如数家珍。
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留下的胶片和设备还有一些“老毛病”。
付德顺说,他们先处理胶片,把胶片上的胶布等处理掉,然后用专门的机器进行洗濯,将胶片上的污垢洗濯掉;如果胶片有断开状况,还要用专用胶水粘合;放映机灯泡和齿皮带等,也须要改换稍好点的新配件。
密云区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中央主任杨海艳提及,他们先期对全区340个镇村落固定影厅和22套流动放映设备进行了排查,对老旧、故障设备进行了检修与改换,以保障展映活动顺利进行。
▲6月27日,坐在银幕前的老人王杖贵。新京报 薄其雨 摄
从胶片电影到数字放映
到6月尾,根据统计,他们已在密云全区放映了7300余场赤色电影。
付德顺回顾,他们刚开始在法制公园播放赤色经典电影《地雷战》时,用的便是刚刚修复好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差错《地雷战》的老胶片。
当统统准备就绪,法制公园里正在遛弯儿的人群陆续围拢过来,险些占满了全体不雅观众席位。
但放映过程并不顺利。胶片放映机是通过两个车轮形状的齿轮拉动胶片的齿孔传动,来实现影片放映。由于放映机和胶片过于老旧,齿皮带多次被烧断,放映过程中屡屡涌现故障,末了只能靠李士龙和付德顺通过手摇拉动齿轮将整部影片播放完。
即便如此,那些看过胶片电影的不雅观众直到影片结束,都迟迟没有散场。付德顺说,“由于怀念,尤其是过去的那些日子。”
付德顺清楚,经历过这次放映后,他很难再见到那些被珍藏的胶片和设备了。在此之后,密云区内所有重温赤色经典的露天电影都用数字放映设备完成。
6月27日这天,虽然是数字放映设备,杨家堡村落的村落民依旧激情亲切不减。
设备调试完,付德顺还保持着坐在放映机旁的习气。“以前放胶片电影习气了,从电影开始到结束,放映机边上一定得有人盯着,怕有闪失落。现在我知道是数字放映了,一按遥控器就没事了,可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的座位半步,我得盯着。”
听说本日放映的影片是《决斗苦战湘江》,村落民王杖贵先一步走到银幕前,他刚干完农活还没来及换衣服,便直接选择席地而坐。
天色未暗,音响中已经传出电影播放的前奏声。
王杖贵朝地上磕了磕自己的铜色烟斗,散落的一撮烟灰泛过一瞬红光后很快熄灭。天色渐晚,银幕上晃动的人影也愈发清晰。
新京报 薄其雨
编辑 左燕燕
校正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