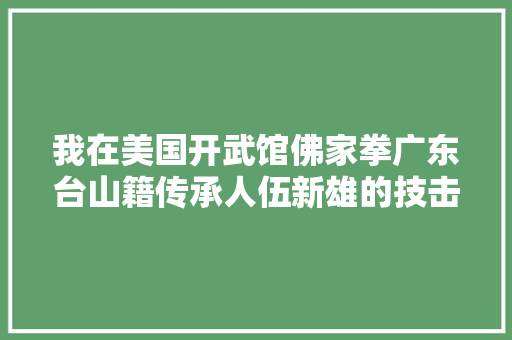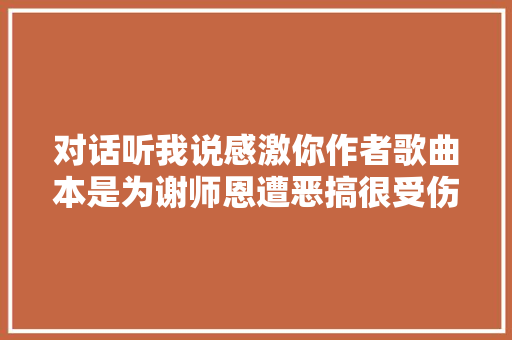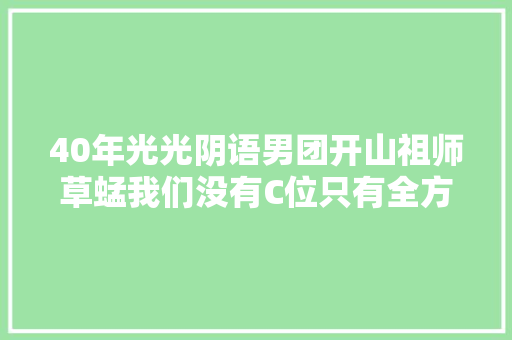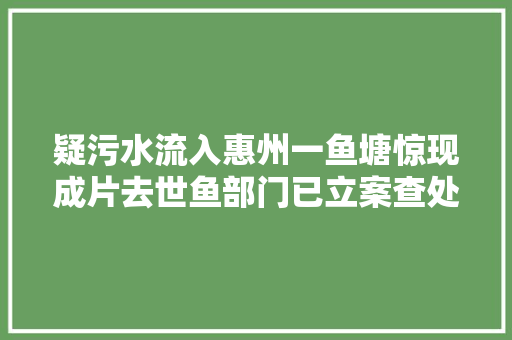12月7日零点刚过,来自台湾的落日飞车乐队在微博官宣,他们正在进行的“夕阳无限好听”巡演将在两天后增加一场广州站的演出。12个小时后,加场门票一开售即被全部秒杀。这是进入12月以来,落日飞车在广州的第6场演出。若算上在深圳刚演完的3场,以及原已售罄、但因当地防疫哀求而延期的2场,半个月内落日飞车在广东地区连续安排了11场专场演出,且全部场次开票即售罄。无论是场次安排,还是市场反应,这次落日飞车在广东地区的专场演出都是海内Livehouse演出市场极为罕见的征象。乐迷们纷纭调侃:“这列落日飞车怕是开不出广东了”“落日飞车是上了粤A牌吧”“夕阳无限加场”。
当人们在评论辩论这几年在大陆兴起的台团热潮时,落日飞车和草东没有派对一定是绕不过的两支台湾乐队。相较于草东没有派对直抒胸臆的“丧里丧气”,落日飞车被打上了“浪漫”“迷幻”“Chill”的标签。这支成团于2009年的乐队,历经草创、发行首专、休团、重组的过山车般旅程后,直到2016年推出仅有三首单曲的EP《Jinji Kikko》,才直冲云霄。他们的歌犹如乐队名字一样,画面感强烈,总能让人遐想到朦胧暖黄的滤镜之下,恋爱的情意绵绵、温顺绸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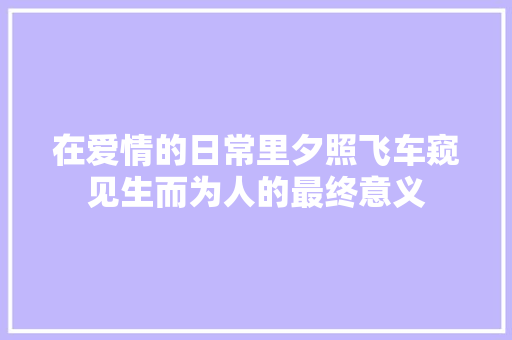
12月1日,在落日飞车开启广州站的6场演出前,南都在乐队下榻的酒店见到了主唱曾国宏(国国)。国国戴着低调的黑框眼镜和鸭舌帽、身穿大略的白色短T现身,看上去和别的台湾男生没什么差异,身为台团热潮的首创者和引领者之一,国国坦言,以英文歌创作为主、目前只有四首中文歌翻唱的落日飞车,“可以在这里红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现在,就让我们来考试测验探索一段他们“匪夷所思”的行进之旅。 采写:南都 钟欣 任婷 演习生 苏悦
未来操持
我们在进行一个新企划,也叫作“夕阳无限好听”,
想翻玩一个老的黑胶观点,会一次性出五张7寸黑胶,
每张黑胶有两首单曲,全体企划统共有十首歌。希望明年夏天可以发布。
巡演火
完备没有想到票房会这么好
面对本次巡演如此喜人(乃至是惊人)的票房成绩,国国说“完备没有想到”。此前从未在同一地区连开这么多个专场的落日飞车,开票之前“实在超级紧张”。直到第一次开票时后台涌入了六万人抢票,国国才以为“我们彷佛是蛮火的”。然而,当这位“蛮火的”乐队主唱终于不须要焦虑票房时,他又开始面对更深层的焦虑了。
南方都邑报:落日飞车这次巡演是一个若何的契机?
国国:我们跟主理单位晓峰音乐公社从2018年开始一贯有稳定互助,我们这次会来紧张也是由于以前双方签下的演出协议。原来我们去年做完新专辑《Soft Storm》就要开始巡回,但由于疫情的关系,一贯没有机会。直到现在这个韶光点,我们以为真的得来,由于新作品已经发了一年,如果再不演,就会很担心这些作品没有吸引力,以是我们决定努力看看。
南都:你们来之前有没有预见到票房成绩会这么好?
国国:完备没有想到。我们来之前实在超级紧张,由于我们两年没有过来巡演,这里乐队“内卷”又特殊严重,以是我们就疑惑,这次过来票还卖得完吗?一开始在广州开3场、深圳开3场,我以为太多了,每场以一千张票来算,每个城市三千张票已是体育馆等级,就很紧张。直到我们官宣巡回的第一张海报出来后,社群的反应才让我以为:噢,这一关该当过得去。
南都:你们在同一个地方密集地连开多场演出,身体或生理上有没碰着困难?
国国:我的困难是我焦虑时总想咳嗽,我就很怕在台上我会边唱边咳。但我这次在深圳演出时创造,我如果上台前喝一点威士忌,演出中间再做一些适量补充的话,就会好很多。
南都:你焦虑的点是什么?
国国:一开始是担心卖票,现在票卖完了,就会担心大家等着看你有没有拉胯,有没有翻车,现在的歌迷都非常严格。还有很多人说,我们这次的票价不算便宜,是大家须要好好方案一下财务状况才可以来看的票价,以是我给自己的哀求是一定要让大家看到很尽兴的演出。但有时这种自我哀求可能太过了,想玩得愉快又担心唱垮了被人骂,想看起来很专业又怕演出不好看,会有这种焦虑。
台团热
我们是从灰烬里重新成长出来的
国国最早在2010年来过大陆,当时没有人在意“你是台湾团或是喷鼻香港团”。直到从同期间成名的草东没有派对和落日飞车开始,“台团热潮”才逐渐形成、升温,经历疫情仍持续不减。身处这股热潮的顶端,国国对以唱英文歌为主的落日飞车能在大陆红感到“匪夷所思”。
南都:近几年在大陆的台团热潮,落日飞车一定是绕不过的名字,你们自己以为为什么台团这几年在大陆这么受欢迎?
国国:如果详细问我台团为什么在这边的反应这么好,实在我不知道。以我的理解,这是一个两岸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你喜好一个人,搞不好不是真的喜好那一个人,你喜好的是你投射出来的形象,台团就成为一个被投射的标的——很多乐迷没来过台湾,但他们可能会以为台湾人便是浪漫、温文尔雅。但实在我们都是“衣冠禽兽”,只是你们还不知道(笑)。
2010年我来大陆的时候,台团完备没有任何吸引力,你是台湾团或是喷鼻香港团都没有人care,没有人会由于你是台湾来的乐队就来看你演出。是从飞车跟草东开始,我才听到有所谓“台团”这个观点,他们怎么剖断草东我不知道,但是以我对飞车的理解,我们的创作以英文歌为主,只有几首中文歌翻唱,以是可以在这里红就已经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红,那真正的欧美乐队就该当更红(笑)。
南都:你说到以为大陆和台湾的乐队会有各自的气质,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国国:我最早是2010年来过大陆,那时候大陆乐队的风格很grunge,大家都落拓不羁,很粗犷,唱的歌词也都很“直球”,不拐弯抹角。乐队演出更像是派对,台上台下玩成一团。
现在的话,最大略的韶光切点是《乐队的夏天》,乃至更早的《中国有嘻哈》,这些节目逐步地将年轻人的文化整合进主流,同时带来成本的参与,让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比如说专业度提升,演出有了SOP(标准事情流程),大家看起来很专业,事情就变得比较干净。我原来以为这样音乐就会变得很不有趣,所谓的“被主流收编”嘛,但我不雅观察大陆乐队创造,也不是这么一回事。虽然说大陆乐队在形式上看起来比较干净,但音乐创作在发达发展,乐风或者乐队的组成多元化。像我上个月在南京碰到Mandarin乐队的吉他手肖骏,虽然年纪个人一些,但技能让人瞠目结舌。他从国外留学回来,现在除了玩乐队,也是音乐学院教授,气质很帅!
我没有想过有人可以一边玩摇滚乐,一边当音乐学院的教授,在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角色存在。
以是我以为,虽然说有所谓的“主流”,所谓的“成本参与”,但是这些资源确实可以让乐队有其余一个发展面向。当然,铁定是要捐躯一些“酷”度或是好玩的程度。
至于台湾的乐队,由于我们的个性便是比较拐弯抹角嘛,我们很怕在台上摇滚的话,别人会以为你很傻,以是有时候我们在音乐的表现上,会有点想发光,但又不敢太亮,大家会比较木木的。
南都:你说的不是那么直接,在我看来正好是种特殊气质,便是所谓的“小清新”“文艺范”,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大陆。但后来到了你们这一代台湾乐队,是不是受到了大陆乐队的影响,也开始变得比较“直球”?
国国:对,有接管大陆乐队的养分。五月天、苏打绿他们有经历过华语乐坛黄金期间系统编制的雕琢或者说演习,而我们这一代乐队经历过台湾音乐家当一个超级低潮的期间,我们是从灰烬里重新成长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任何主流音乐的演习,乃至连乐器也没有弹得很好。我以为从五月天、苏打绿到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乐队,气质上也有很大的断层。
在草东前面是“小清新”称霸的时期,当浪潮开始转向,你要么做出一个完备对立的乐风,要么便是从“小清新”里质变。草东是完备对立的乐风,一定要把愤怒、沮丧发泄出来。而飞车是从“小清新”里质变的乐团,我们还是一种“清新”,但我们比较没有focus在缥缈的哲学探索上,我们更倾向中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追求:喝一杯好喝的咖啡、住一个超爽的饭店、吃一份大餐——你对未来已经没有什么要特殊奋斗的事,不如享受当下的物质和欢愉。
浪漫派
我的浪漫都贡献在音乐里
在乐迷的眼中,落日飞车是“浪漫”的代名词,无数人从他们的歌里投射关于爱情的美好想象。然而,国国说自己没有刻意描写爱情,而是希望从爱情的详细日常里“窥见生而为人的终极意义”。
当被问到自己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时,国国绝不犹豫地回答“超级不是”,他相信“浪漫守恒定律”。他称自己为“意志的美食家”——永久无聊地只乐意考试测验之前吃过的几样东西。这让我们想起在采访开始前,经纪人不假思虑地帮国国点了一杯热美式。大概,能写出这么多给予别人浪漫想象的歌曲,便是他做过的最浪漫的事。
南都:你怎么看待大家给落日飞车的“浪漫”标签?
国国:飞车大部分的歌都是我写的,我只要参与创作,就会有飞车的氛围。虽然我也不以为这就叫“浪漫”,但如果市场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叫作“浪漫”的话,那我写的东西便是偏浪漫。
南都:你本人在生活中是浪漫的人吗?
国国:我超级不是,我实在蛮无聊的,我很常开玩笑说我是“意志的美食家”——我会用我的意志来决定一个东西好不好吃,而不是来自于客不雅观或者比较之后的结果。比如我吃东西只吃之前吃过的那几样,纵然别人说其他东西很好吃,我也不会想去考试测验。再比如我打电脑游戏,我就一贯打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玩、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的《星海争霸》(大陆名为《星际争霸》),便是玩一个安全感。
南都:你真的没有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
国国:(沉思许久)我以为真的没有,我的浪漫都贡献在音乐里,这句话是真的。想一想也是公正的吧,如果我的生活也都超级浪漫,那我写的歌铁定超无聊。我是天秤座,以是我很看重平衡,当我的生活开始有浪漫气息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糟了糟了,生活要从我的艺术中剥夺我的浪漫元素了。
南都:飞车的歌大部分和爱情有关,你的生活这么无聊,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国国:我自己没有刻意去写爱情,比如我想写关于遗憾和希望,爱情便是一个很好的被叙事的主体,但我想谈论的事情不尽然是爱情。我不会去写过于抽象或过于哲学的东西,我希望从爱情当中一些很详细、很日常生活的事情,可以窥见生而为人的终极意义。
我很喜好一个作家叫雷蒙·卡佛,他的书利用最大略的文法和用词,可他的叙事很有分量和冲击力。他写的短篇小说大都讲述市井小民的生活,每个故事一定会有情侣或者夫妻,爱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它谈论的主题常日跟人、生活、文化有关系,爱情只是底色,这是我自己很喜好、也很适宜我的叙事办法。
南都:你空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国国:我以为最棒的爱情该当是双方共同发展。大多数人对付爱情会有一个浪漫的定格画面,但两个人相处久了会有一个“除魅”的过程。如果双方发展都结束了,就会创造对方很无聊,爱情要双方一起发展才不会腻。